《黄昏,闭上了眼》:我的眼睛在黑夜中闪耀
来源:中华读书报 | 莫莹萍 2019年12月15日09: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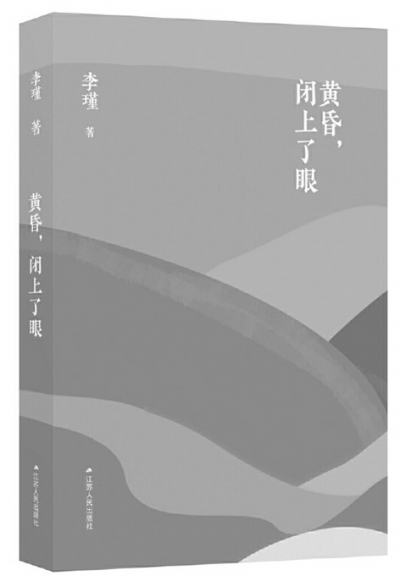
《黄昏,闭上了眼》,李瑾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10月第一版,49.00元
《黄昏,闭上了眼》是李瑾个人第三部诗集,此次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推出,作为责任编辑,我是以“手术刀”的角色深入诗集中的篇章字句的。该书出版后,作为除作者之外最熟悉文本的阅读者,觉得有一些体验需要谈谈。我的整体感受是,这本在朝夕两端、往返之途的地铁中用电子笔记本写就的诗集,依旧是李瑾“在地铁中体验世界的不安,在地下观照地上的产物”。
我们通常会说“诗缘情”,但情和志其实很难分离而论。就李瑾的创作而言,无论情还是志,都不存在主题先行的问题,亦即在他的诗歌中,两者都是发生学意义上的,而不是功能论意义上的。这就是说,李瑾的个人创作善于“造橱立柜”,善于把自己经历的生活百态、情爱忧思、山川游赏、书斋文海统统装进自己的情感之中。
关于诗歌的形式和自由问题,李瑾有自己的独特认识,他认为:“新诗无疑是诗人确立自我身份的尺度。这个意义上,新诗与真理、民族乃至人类是合一的。也就是说,当谈论起源意义上的新诗时,一定是在抛弃古诗/传统——这种讲究格律的语言集束,充满了压抑、束缚,在表达上捆绑了诗人的身体。而新诗则是奔放澎湃的、可吞日月的,诗人吟咏‘我是一只天狗’之际,其和新诗同体了,他们统为自由的象征。经由诸代诗人谱写,新诗升格为自由的神话。”通常而言,诗歌不同于其他文学载体的一大特性即是自由,首先表现为形式的自由,尤其是脱离格律等形式束缚的新诗。在形式上,李瑾诗歌的自由性又更进了一步。他喜欢使用断裂式的跨行形式,把上一句末尾的词语抛到下一行开头,不仅使诗歌在音律上有了更强的节奏感,版式上更具形式美,而且在空间上营造了更强的纵深感。
例如,《宣武门教堂》一篇:“仿佛人间是一道隐形的皱褶。五叶槭/停在半空中,教堂的尖顶攥紧了白云/间或有行人打门前/经过,受难者才敛一敛/绛色的衣襟。我们都活在自己的体内/没多少悲伤,除灵魂偶尔出窍,钟声/偶尔将格子窗推开/一切都不是尘世的。在/教堂前,祈祷无关紧要,忏悔也没有/多少份量,它和人类一样,有砖型的//结构,以及超出自己真相的玻璃皮囊”。这种断裂式的跨行所产生的停顿又像是中国古典园林中的障景艺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悬念对读者有着强烈的吸引力,而呼之欲出的点睛之词也从未让读者失望,读来非但没有滞涩之感,反而感觉酣畅淋漓。
我们身处的人间有不可胜数的条条框框和“金科玉律”,万事万物都被假以规律、真理、常识严实地包裹着我们的生活,一种被规训的、不自由之感时时困扰着我们。但在李瑾的诗歌中,这种束缚感被“自然”(和谐的外在之境)同化了。这个意义上,李瑾是十分契合“自然诗人”的称谓的。翻开李瑾的作品,沉浸其中,很容易获得这样的体验:山川在我的怀抱,河流在我的身体里流淌,我的眼睛在黑夜中闪耀,我的鼾声在雨天打响,自然是我,我是自然。也就是说,在诗歌中,李瑾的自由性和自然性紧密地连接在一起。这一点,在解读庄子的《逍遥游》这一篇什中体现得最为淋漓:“时间过于玄远,只能自/黄昏抽身,自夏日抽身/一点一点落在生活之中/生活之中,人间是安全的,阳光是稳定的/我的消失也是波澜不惊的。我不拘泥于水/一些水已陷入河流/另一些站在平原内微微起伏/我身体里的水漫过了椰子树,椰子树饱含/热泪,迷恋着清醒与混沌的疆域,疆域啊/无法回避罪恶,也无法回避比生命尖锐的/东西。我不妄言无穷,我只存在或者离去/命运太弱/我痴心于逍遥,痴心于短暂且致命的幸福”。通读诗集,我感觉李瑾写诗就像一位纯真的孩童拿着蜡笔,恣意地涂抹着自己的内心世界。当然诗歌是极其私人的“语言”。作为责任编辑,我不刻意寻找言语中“蛛丝马迹”,也不敢妄言我读懂了什么,但我读出了我的困境、疑惑和豁然开朗这般的“感同身受”。
李瑾喜欢在自然之中寻找事物之间的本质联系,狡黠的他又利用自然之口,把自己的所思所想向外界发声。试举一例,秋季的落叶是他所钟情的意象。在他的笔下,落叶“不外乎一种秩序/接纳了春天,然后一点点地将它交出”。面对四时变换,自然如此豁达,人类亦如此,“斗转星移,潮起潮落,既在我们心中/更是我们的身外之物”(《景物如果是一种不过如此的态度》)。纷飞的落叶又像是在向世人诉说“要么学会生芽,要么学会隐藏自己的寒骨”(《时光从容,却难以原谅》)。
不得不说,在审读《黄昏,闭上了眼》时,我重新梳理了个人的精神纹理,即为什么阅读诗歌和为什么需要诗歌。我给自己的一个答案是,因为我们需要幻想、远方和虽不存在却可以提供情感慰藉的“乌托邦”:日夜奔走于尘土之中,声利扰扰,尘埃零杂落了一身。只有翻阅李瑾这类诗人的作品,才能在沉思中细细抚去身上的万般尘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