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法国读者浅谈曹雪芹的《红楼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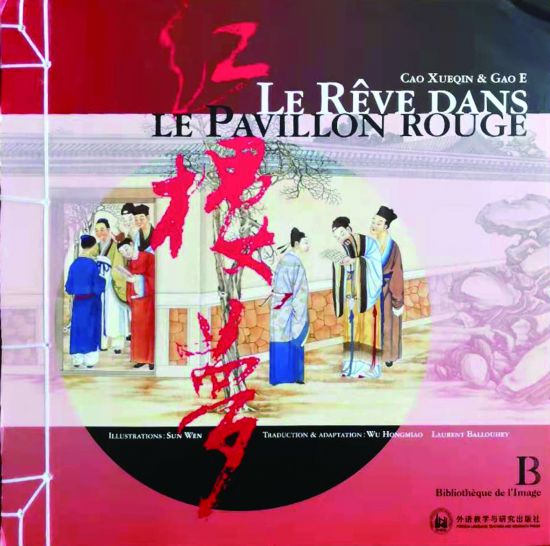
《红楼梦》法译绘图本封面(2017年)和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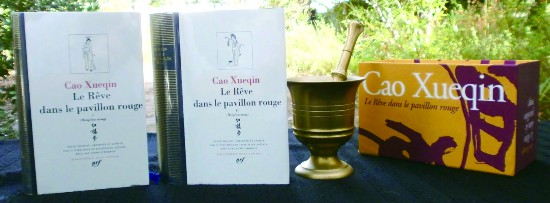
李治华、雅歌合译 铎尔蒙审校版《红楼梦》,七星文库出版
《红楼梦》出现于18世纪清朝乾隆年间。小说开篇,一个跛足道人吟唱他的“好了歌”,甄士隐配上一首“释义诗”,构成了这部中国古典名著的“主导动机”,引领读者深思大文豪曹雪芹富于哲理的人生观。
谈及《红楼梦》一书起源,要追溯到女娲炼石补天之时。一块女娲未用之石遭弃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因为不得入选自怨自愧。不知过了几世几劫,这块顽石被茫茫大士携入红尘,在人间历经一番幻梦,遂成小说《红楼梦》。此书中,作者用“梦”、“幻”二字作喻,巧弄玄虚,其实是录红尘情事,自色悟空,让阅者对人的异化现象觉醒,走向“彼岸”。至于寄人篱下的孤女林黛玉,她的厄运让人想到莎士比亚笔下西方世界的“奥菲丽娅现象”,更具体的形象是安徒生《海的女儿》里小美人鱼渴望人间幸福,最终在所爱王子新婚之夜化成了大海的泡沫。所有追求绝对幸福的情种,大凡都遭遇这般凄凉结局,落入空华。
幻梦本是人们向往的征象,自古以来,在文学修辞上始终被看作一种隐喻。东晋“桃花源”诗人陶渊明就有“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之说,苏东坡亦有“古今如梦,何曾梦觉”的名句。在中国,梦乃是一幻觉修辞格,许多文坛秀士倾向描绘梦境,追溯畴昔。譬如,唐朝李公佐《南柯太守传》,写淳于棼醉卧槐树下,梦入蚁穴,当了蚂蚁王国南柯郡太守,结果是场梦。唐代另一文人沈既济的传奇小说《枕中记》,也描述一个卢姓儒生在旅途中下榻客栈,遇道授枕入梦,历尽荣华,醒后悟出自己做了一场空梦,产生“人生若梦”的意念。明朝汤显祖据之写出戏曲《南柯记》,显示作者“看破红尘”的道家出世思想。尚有清朝俞达的说部《青楼梦》和《金屋梦》(亦称《隔帘花影》),后者系《金瓶梅》的续集。
中国最负盛名的“释梦”小说,当数曹雪芹的长篇巨著《红楼梦》。在法国已有数种译本,较早的是1964年阿赫麦勒·盖尔奈(Armel Guerne)从德国翻译家弗朗兹·库恩(Franz Kuhn)的德文版转译,上下两册,1964年由巴黎吉勒普拉书局(éd.Guy Le Prat)印行。其他分别于2015、2017和2019年出版的三种法译本均为绘图普及版。真正的纯文学译著是由“七星文库”推出的李治华、雅歌夫妇合译的120回全译本《Le Rêve dans le pavillon rouge》。
读《红楼梦》,笔者联想起西班牙剧作家彼得罗·卡尔德龙(Pedro Calderon,1600-1681)的欧罗巴文学名著《人生如梦》(La vie est un songe)。17世纪西方的卡尔德龙同18世纪东方的曹雪芹一样,都有世人生活在梦中的感受,“浮生若梦”,或像卡氏所云:“人生如戏”,一种再通俗不过的世界观。卡尔德龙的《人生如梦》里,波兰国王巴希尔为防止儿子西吉斯蒙在他生时篡位,将他关进一座坟墓般的塔楼。西吉斯蒙登基后,对其父并没有以眼还眼。他悟出人世间的真缔,即人的所有痛苦都会转瞬即逝,一切都是“镜里花,水中月”。从这层意义上说,将曹雪芹的小说译成“rêve”(Le Rêve dans le pavillon rouge),不如采纳卡尔德龙的“songe”一词。弗洛伊德在“释梦”中说,“rêve”是“要实现一种意愿”,指人在梦里看见的幻象。法国象征派诗人纳尔华指出,实际生活的“流露”,应为“songe”。曹雪芹的《红楼梦》乃是他一生怀旧的追思,“昨夜朱楼昔日旧梦”,一种“人生如梦”的流露,而非向往未来的梦想,并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rêve”,故移译为“songe”更为恰切。
《红楼梦》出现于18世纪中国清朝乾隆年间,是划时代的文学经典。从修辞角度看,“红楼”是人类境遇的意象,有深厚的象征色彩。“梦”影射人希望的幻灭。这部作品起始取名《石头记》,确切地说是一颗陨星的轶事。后来,作者将之改称《金陵十二钗》,直至现今命名的《红楼梦》。这原本是小说主人公贾宝玉神游太虚境,警幻仙姑令十二素练霓衣舞女歌唱的曲调名,敷演一场“开启鸿蒙”、“悲金悼玉”的幻梦。小说叙述十二位仙女降落红尘的经历,尤其是林黛玉、薛宝钗与贾宝玉凄惨的爱情纠葛。这三个小说主要人物中,薛宝钗的现法文译名似欠斟酌。薛宝钗生时颈上挂着一个金锁,上有“金玉良缘”四字。她的法文芳名自然应译为“金钗”(épingle d’or),而非眼下直译的“宝钗”(épingle précieuse),脱离了贯穿整个故事的情节。
小说《红楼梦》贯穿一个凄楚的“三角恋”。贾宝玉命定是要跟薛宝钗结“金玉良缘”的,但是他偏爱上了林黛玉,遭贾母激烈反对。“老祖宗”按王熙凤献的巧计,安排贾宝玉婚事时,用薛宝钗换林黛玉来欺诓孙子。真相在洞房花烛之夜暴露,新郎发现受骗,痛心疾首,最后撇下贤妻,跟僧道二者出家当了和尚。贾宝玉终了出走,表明他深深厌恶贾家人伦关系的虚伪。“红楼”梦破,心归菩提。
涉及到翻译,有句意大利谚语说:“Traduire,c’est trahir”。意思是,要做到严复所谓的“信、达、雅”,从文学上是不可能的,想按鸠摩罗什的“依实出华”,更是难上加难。像《红楼梦》这样的中国古典巨著,严格说来是不可移译的。因而,一些法国读者依据现有的几种《红楼梦》法译本衡量,断言曹雪芹的巨著“够不上世界文学经典”。显然,这是忽略了中西方文学之间有着巨大的文明差异,存在几乎不可逾越的鸿沟。应该承认,《红楼梦》无论是法译本,或是英译本,都不可避免地存在误译,导致西方读者“误读”,产生对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偏见。
西方人翻译《红楼梦》,首先遇到语言难点,出错在所难免。最早的英译者乔利将“好了歌”中古今将相死后“荒冢一堆草没了”,翻成:“Waste lie their graves,a heap of grass, extinct”。这里,译者将“荒冢一堆”译成“一堆荒草”(a heap of grass),并不全是作者要呈现的意象。当然,此处只是细节上的差错,更为严重的是,翻译中往往出现理解问题,曲解原意,这在一些《红楼梦》法译本里屡见不鲜。譬如,《金陵十二钗》题曰:“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不久前,一位法国译者将“谁解其中味?”译成“谁尝得出其中的甜蜜味”。曹雪芹明言自己叙述的奇传是“一把辛酸泪”,像胆汁(le fiel)一般苦涩。译成“le miel”(蜜),无疑违背了作者想阐明的“要旨”。汉学家铎尔蒙译解为“Mais qui saura goûter le suc qu’il assimile?”虽略胜一筹,但“le suc”一词意为“精华”,也没能反映出《红楼梦》本是一部“还泪”小说。笔者以为,倒不如干脆改为表达“苦涩”的“le sel”(盐),包含“精华”词义,更多是“咸”,即“辛酸”。一字之差,牵动全局,改变整部作品的色调。
2014年,在纪念杰出翻译家谭霞客(Jacques Dars,1937-2010)病逝4周年之际,巴黎关注中国文学经典的文论界发出了重译曹雪芹《红楼梦》的呼声,称《红楼梦》是“一部有待重译的杰作”。早先,法国汉学泰斗勒内·艾田蒲在委托李治华翻译《红楼梦》时,还推荐谭霞客译《水浒》,但法国文学界及受众对二者译作的褒贬悬殊,原因大概有多方面,不须赘述。
谭霞客生时撰文《译无止境》,他分析文学翻译之难,难在其“不可转移性”,尤其在移译过程中难以保持原来的美学特征。譬如,汉语文字转化为拉丁拼音字母,必然会失去形象美,造成视觉感受的缺失,是不可避免的。至于移译采用文言书写的古典文学作品,势必会出现文学的赤贫化,丢失原作丰富的意象和神秘特征,翻译者恰如歌德所云,是“自投束缚”,不可能达到自然完美的程度。出于上述原因,具体论及“七星文库”推出的《红楼梦》法译本,谭霞客认为它“谈不上精当”,远不是最后可以被人认可的佳作。首先,这一译本的法文名称“就是一个‘穷窘’的表达”,需要再斟酌。谭霞客分析“红楼梦”这个题名,说:“‘红楼’是少女的闺阁。以此为题,显然有双重怀旧的底蕴,即昔日的富丽堂皇仿佛一场梦幻,一个对作者华年结识和爱恋的闺秀追怀的冥思苦索。”
清末小说家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法译者黎诗薇赞同谭霞客的倡议。她认为,“七星文库”的《红楼梦》法文版不仅仅有题目问题,明确提出“这部杰作需要重译”。照她看来,原作里每个人物都有自己鲜明的性格,“但从李治华的翻译中难以感知他们个性和谈吐的差别,而且译文的风格既死板又累赘,将原来十分流畅的对话翻得极为呆板,陷入了难懂的句型泥潭”。为了证实这一缺陷,黎诗薇重译了两段贾宝玉与林黛玉的对话,公开发表。对这一法译本的非难远不止于此。法国女作家苏珊·贝尔纳对它甚至采取了基本否定的态度。她举例说,将贾政译成“贾政治”(Jia politique)实在可笑,并声称挑出其中不少基本的法语语法错误,结论:“这一法译本毁了一部中国古典名著。”此种苛求对用了整整27年工夫、与法国妻子雅歌(Jacqueline Alézaïs)合译出《红楼梦》的李治华先生显然有失公允。况且,其中还有不少人们尚不知晓的因素。
1985年夏天,我用法文撰写的长篇小说《悬崖百合》在巴黎出版,本人应邀到里昂和圣·安德烈奥勒等地做相关报告。李治华先生亲自到里昂火车站接我,邀我在一家中餐馆共进午餐。他是一位极其热诚又谦逊的翻译家,我们俩畅谈了整整3个小时。那次长谈中,他回述了自己与妻子花了20多年心血翻译《红楼梦》的详细过程,吐露作为译者的苦衷。他向我坦言,他们夫妇俩最初的译文与“七星文库”最终出版的《红楼梦》法译本相比,被改得“面目全非”,尤其是诗歌译文部分,“不见原来丝毫踪影”;实际上是铎尔蒙先生将他自己的译文和盘托出了。
安德烈·铎尔蒙(André d’Hormon,1881-1968)是李治华的老师,自令后辈存感戴之心。铎尔蒙系法国文人,曾在中国生活多年,寓居北京香山时是法国名医贝熙业大夫(Jean-Auguste Bussière)家中常客。他1955年返回法国,为李治华所译《红楼梦》改稿,直至1968年谢世为止。“披阅十载”,可以说是为这部中国古典名著“沥尽心血”,功不可没。但汉语毕竟不是他的母语,何况面对汉字复杂的笔画,包含深邃底蕴的文言,他自有鞭长莫及之虞,难免会用法国文学传统的眼光去审视中华传统文学,在掌握语言方面的过分自信。铎尔蒙翻译的《红楼梦》“序言”、“好了歌”和甄士隐的《“好了歌”释义》诗,都是很值得推敲的。
曹雪芹的“好了歌”和甄氏“释义诗”,皆有自然韵律节奏,近似两首民谣。但铎尔蒙的译诗相当生硬,勉强押韵,全无中国古诗朗朗上口的流畅和抑扬铿锵节调,倒恰如法文所云“硬得像骨头一般”,在文学上不可取。更突出的是,“好了歌”竟被译成了“Chanson de la bonne fin”,无意中将“好”与“了”两个本是独立的关键词合成了一个概念“la bonne fin”,势必让西方读者从语感上将之误解为一首“善终歌”。这完全不是跛足道人要表达的真意:“可知世上万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了,须是了。”如此这般阐释,“好了歌”被直译为“善终歌”,走得似近却远,曲解了曹雪芹表达的宇宙人生观。此一误译难免不会造成法语国家受众的严重误读。铎尔蒙先生的“好了歌”译文中尚有其他误译,例如“他乡”被直译成“他人的故乡”(la patrie d’autrui),将原指“新婚夫妻”的“鸳鸯”泛译为“情侣”(un couple d’amants)之类,因韵害义。
“好了歌”是《红楼梦》全书的“主导线索”,一个引人走出迷宫的阿丽亚娜线球。故笔者在跟法国读者谈论这部文学经典时,不得不将铎尔蒙译的《Chanson de la bonne fin》换成《Chanson de la vanité》,即将“善终”改为“虚幻”,使之符合整部小说的“主旨”,并随之将“好了歌”全文以及甄士隐的“释义诗”重新翻译,以期在法式“大观园”里移植进一对山野灌木丛中的《棠棣之花》。
在穷儒寒士贾雨村“归结红楼梦”最后一回里,贾政听见僧道口中不知是哪个作歌曰:“渺渺茫茫,归彼大荒!”他“不能洞悉明白”三千大千世界,只见“白茫茫一片旷野……”正应了《红楼梦》作者所云:“古今一梦尽荒唐”。
谚曰:“人生如戏。”法国文豪巴尔扎克文集总题为《人间喜剧》,正是这层意思,与曹雪芹通过跛足道人之口化用的是同一种世界观,展示的是国学大家王国维感受到“人间悲剧”的寂灭。
- 刘心武探索曹雪芹的花木世界[2021-05-28]
- 《红楼梦》中的酒令:雅音俗韵,隽永深长[2021-05-23]
- 如何理解《红楼梦》中的“烫蜡钉朱”?[2021-04-22]
- “从《诗经》到《红楼梦》”古籍展开展[2021-04-14]
- 《石头记》甲戌本归去来[2021-04-12]
- 《红楼梦考证》百年:重审胡适与蔡元培的论辩[2021-03-29]
- 《金瓶梅》和《红楼梦》里的酒局[2021-03-22]
- 贾雨村对贾宝玉人生的隐喻意义[2021-03-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