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金论童话:“第二创造者”和他笔下的奇境
J.R.R.托尔金,英国作家、语言学家,被公认为“现代奇幻文学之父”,其代表作《魔戒》三部曲蜚声四海。
《论童话故事》(On Fairy-stories)是1939年托尔金应邀在圣·安德鲁斯大学所做的演讲(后收入《致查尔斯·威廉姆斯的文章》一书),彼时《霍比特人》业已出版,而《魔戒》正在创作中。托尔金曾在一封信中表示,对于任何想要理解其文学的人来说,《论童话故事》都是“相当重要的作品”,评论家也相信它构成了魔戒小说的理论基础。

J.R.R.托尔金
何为童话:创造“第二世界”
童话在英语里的对译词是“fairy tale”,字面意思为“关于小仙子(fairy)的故事”。这个释义显然太过狭窄,因此对于“童话是什么”这个问题,托尔金试图给出另一个回答。
托尔金认为,直接讲述小仙子的故事是很少见的,更多的童话其实是在叙述凡人“在危险之地的神秘冒险”。在他看来,童话故事(fairy-story)首先不是有关精灵、仙子这些神奇生物,而是关乎“奇境(Faerie)”,即精灵、仙子所栖居的领域,这个领域所含更广:天地日月,草木鸟兽,无所不包;甚至人类自己,当我们陶醉于此世界的魔力时,也能够栖身其间。因此托尔金论说道,真正的童话只能是那些言及“奇境”的故事,不论其写作目的是出于幻想还是讽喻,关键在于如何创造、呈现那个“奇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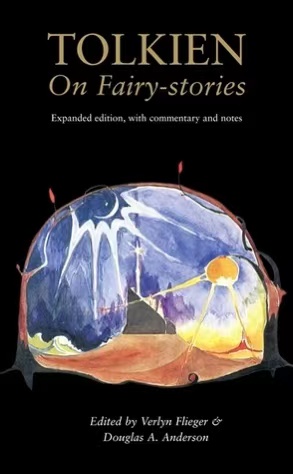
《论童话故事》(扩充版)图书封面
论及童话的起源时,托尔金的思考则触及了一些有关哲学或人类学的问题。相较于部分学者认定神话是人类语言的产物,托尔金却认为语言反倒是神话(以及一切幻想类文学)的结果,“去追问故事的起源,就是去追问语言和心灵的起源”,因为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原点,心灵、想象和语言三者本就是彼此统一、相互融合的。童话自始至终就伴随着人类,它是一项专属于人、意义重大的活动,由于创作童话意味着呈现出一个世界、“奇境”,因此童话可谓一种真实的创造,一种相对于上帝创世而言的“第二创造”(sub-creation):
在童话故事中作者证明自己是一位成功的“第二创造者”(sub-creator)。他创造了一个“第二世界”(Secondary World)供你的心灵进入。在这个世界里,他所叙述的都是“真实的”,符合世界本身的法则。因此当你置身于其间,你相信一切尽如是。一旦你有所怀疑,咒语就被打破了,魔法,或者不妨说艺术,便沦为失败品。于是你又退回到那“第一世界”(Primary World)中去,从外面打量着那个小巧却不成功的“第二世界”。
就像宇宙万物是上帝的创造一样,童话的奇境则是人类自己的创造。童话故事呈现了一个人们可以进入并信其为真的“第二世界”(托尔金有时也称之为“异域他乡”):真实感取决于读者不自觉的相信,而不是如柯勒律治所说需要时刻提醒自己“悬置怀疑之心”,只有真正参与、沉浸到童话故事之中,才能把它当作内在统一的世界来体验。面对有关童话是自我欺骗的一类指责,托尔金则表示,比起“这是真的吗?”,更重要的问题其实是角色的善恶问题:他特别强调,童话故事的首要关切不是“第一世界”中何事可能发生,而是何物可欲;换言之,童话故事关乎人类存在的诸多原始欲望,比如探索时空的深度,比如与世上的其他生命相交流,“如果童话故事能够激起人的欲望,并在难忍的刺激中满足它,则童话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既然童话所满足的正是人类自身深蕴的欲望,那么幻想文学就为每一个时代所需要,所谓“神话是儿童期的人类文明的产品”的人类学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由此一来,托尔金便驳斥了那种认为“只有小孩子才看童话”的习见:我们不能认为童话的存在只是利用了儿童特有的轻信心理,仿佛只有他们身上才保留着信任感和奇迹感,那无异于是说这些珍贵的精神品质在成人的现实世界中荡然无存。事实上,童话被视作儿童的专属品,只是西方社会家庭史的一个偶然结果。对“第一世界”的理智认识并无害于艺术想象的冲动,于是托尔金指出“童心”(the heart of child)对成人来说也是必要的,要开启在奇境中的旅程就须心怀谦逊和纯真。因此成年人面对童话,不应把它视为幼稚的文字,而应当成是文学的一个自然分支来阅读。
童话在今天的价值
为了捍卫童话(或者说一切幻想文学)在现代生活中的地位,托尔金需要澄清这一体裁的各种功能。他认为童话具有幻想、复苏、逃避、慰藉四种价值,关于这些价值的描述进一步阐明了托尔金对童话的理解,特别是如何在今天创作出一部成功的童话。
童话的第一种价值是幻想(fantasy)。幻想不是简单的、任意的想象,而是要利用艺术的头脑赋予纷繁复杂的想象物一种内在的统一,唯有这样才能唤起读者对“第二创造”的信任感。因而真正的幻想必然总是艺术性的。托尔金还强调,推崇幻想并不等于贬低理性知识的地位;恰恰相反,清晰的理智更有利于创造真正的幻想,因为只有恰当的理性才能避免一个人的幻想流于病态的幻觉,“创造性的幻想建立在对事物真实模样的承认的基础上;注意,是对事实的承认,而不是对它的驯顺”。归根结底,幻想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活动,是人的权利,因为从一种宗教的观点看,人类本身就是按照造物主的模样创造出来的,人类也因此分享了创造的禀赋,毕竟童话就是幻想,就是心灵和语言的创造。
真正的幻想应当有其专属的表达手段,那就是文学。“第二世界”的创造最好交由文字来实现,而其他具有视觉性的艺术形式(比如绘画)所呈现的奇观都可能流于肤浅;甚至连舞台剧也不适合幻想,因为可视化的舞台元素会偏离故事的讲述,并且会把故事牢牢限定在舞台演出的范围内。在托尔金看来,文学和其他艺术形式的区别就在于后者会强加一个视觉形式,从而限制了观众的个人想象:比如童话里写道“他爬上山,看到了山谷中的一条河”,这句话包含了一切可能的联想和蕴意,不同读者都能根据自己曾见过的山与河,在心中描绘出各不相同的画面,但绘制插图的人只能勉强呈现出单一的图景。文学语言可以在心灵与心灵之间流转,它更具有普遍性,同时又与个体的经验密切相关。如此来看,不知托尔金会对21世纪风靡全球的《指环王》系列电影作何感想,总之强调文字表达有利于幻想,可能暗示了童话故事更需要读者私人化的参与和沉浸。
童话的第二种价值是复苏(recovery)。童话虽然从“第一世界”中汲取材料,但是却能让人们以新的眼光去看待它们:“正是在童话中我才第一次预知了语言的能量和事物的奇迹,比如石、木、铁;树木与花草;房屋与火焰;面包与醇酒。”复苏,就意味着重新激活人类的经验,童话的艺术创造能够擦拭心灵的窗户,帮助我们更好地看到万物的原初面貌。
童话的第三种价值是逃避(escape)。不妨将童话的逃避功能比作“越狱”,逃离所谓“现实世界”的铁笼:对于那些太久深陷于如其所是的“第一世界”、沉湎在去魅的社会生活中的人来说,童话是有益的,是一种解放——越狱之后便是回家:童话激励人们逃避到生活的另一个维度,一个超越了事物之实际所是、超越了过分机械化的现代生活的幻想维度,它帮助我们重新欣赏作为整体的自然。据托尔金所言,童话绝对不是在鼓励人们消极避世,或罔顾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责任,因为进入“第二世界”是一种良性的逃避,它的冲动源于对现世丑恶的抗拒,源于对人类的根本欲望遭受压抑的不满;更积极地说,逃避的冲动源于对一片呵护着人类的心灵和想象力的家园的向往,这个家园保证我们与身上的人性、同时也与自然中的其他生命和谐统一。

Alan Lee为《魔戒》所绘插图
童话的第四种价值是慰藉(consolation)。童话通过书写“大团圆结局”(the happy ending)来慰藉读者的心灵。为此托尔金创造了一个词“eucatastrophe”,意谓“好的灾难”:在悲剧即将发生的时候迎来转折,把故事重新引向令人快乐的结局,即讲述“一次突然的、奇迹般的恩典,不指望它会发生第二次”。真正的童话都应该表现“好的灾难”,这并不意味着漠视悲剧的存在,恰恰相反,只有充分描绘了极端困境给人带来的痛苦,后文的剧情转折才能给人以快乐,才能充分发挥慰藉作用,就像《王者归来》的末尾,弗罗多和山姆被困末日火山,眼看就要葬身火海,此时巨鹰首领关赫突然现身,成功救下了二人。童话——关于“好的灾难”的故事——就好比一份信念,相信人类的希望不会落空,相信人类所盼望的美好事物终有一天能够实现。因此所谓圆满结局并非虚假的自我安慰,快乐不仅产生于人物悲剧的解除,更产生于在这个福音般的转折中对真理的一瞥。
民族神话,或普世的幻想文学
在《论童话故事》里,托尔金对童话体裁进行了崭新的界定,这些描述俨然迥异于通行的、为幼儿所写的童话作品,诸如“真理”、“创造”、“原始欲望”等词语赋予童话写作一种远为宏大的视野。因此有不少人认为托尔金等于是将童话重新解释为神话(myth),作家本人在文章里也频繁提及这个概念——我们不妨把《论童话故事》看作对一切幻想文学的宏观阐述,使用单一的概念“童话”却不限于讨论一种文体,毕竟童话、神话、传奇在人类历史中原本都是相互召唤的,类似周作人在《童话略论》里所言:“童话(Märchen)本质与神话(Mythos)世说(Saga)实为一体……童话者,于此同物,但意主传奇,其时代人地皆无定名,以供娱乐为主,是其区别。盖约言之,神话者原人之宗教,世说者其历史,而童话则其文学也。”
狭义的神话指有关神灵的故事;这肯定不是托尔金所思所想,他口中的神话其实更接近于《埃达》、《贝奥武夫》那样的传奇故事(lengendarium)。托尔金对神话的兴趣源自他所从事的中世纪语言文学研究,他很早就萌生了自己撰写一部神话的念头。为了应对混乱、碎片化的现代性经验,20世纪作家如詹姆斯·乔伊斯、T.S.艾略特等人都不约而同地乞灵于往昔的神话,以便用它赋予现代生活某种秩序感——托尔金也当属此列,只是他对于为何有必要在今天写作神话抱有更具体的动机。在1955年的一封信中,托尔金谈及自己的神话创作是为了给他当时出于爱好所发明的语言(即精灵语Elvish)打造一个故事背景:“语言的发明是(小说的)根底;那些故事都是为了给这个语言提供一个世界,而不是相反。”而在另一封致出版社编辑沃尔德曼的信里,托尔金则表述了他早年从事写作的民族主义动机:
曾经我有想(这个冲动久已消退)去写一系列多少是相互联系的传奇故事,从宏大的宇宙诗篇,到浪漫的童话故事,不一而足……我只会把这些传奇故事献给英格兰,我的祖国。它们应该具有我想要的那种语调和品质,有些清凉和澄澈,使人想起我们这边的“氛围”(是英格兰、欧洲西北部的气候和土壤:不是意大利或爱琴海,也不会是东方)。
在他看来,英格兰没有像《罗兰之歌》、《尼伯龙根之歌》那样的神话,没有同自己的语言、土壤息息相关的英雄故事,这让身为盎格鲁-萨克逊语教授的托尔金在其他民族史诗面前感到沮丧不已。这就是为何托尔金格外钟情于《贝奥武夫》,一部讲述丹麦人事迹、但却只留存下古英语抄本的民族神话,他曾明确表示《贝奥武夫》是《魔戒》系列小说最重要的资源,并且也不遗余力地把这部神话诠释为英语文学的一个源头。所以按照托尔金早期的构想,《魔戒》全书几乎可以看作是写给英国、献给英国的现代神话。
不过,正如托尔金自己所说,这种动机后来已经消退了,主导其童话/神话写作的不再是爱国情结。托尔金后来逐渐发掘了幻想文学和基督教神学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让他意识到他的文学写作可能具有超越国界的意义:他开始相信,童话、神话以及一切类似的幻想故事,在一定程度上都能成为基督教所谈的“真理”的表征。这就为他钻研外族神话、自己动笔创作新的神话提供了充分的理由:
我相信传说和神话主要都是由“真理”所构成,并且“真理”的某些方面只在这种故事模式中才能被感知。很久以前,特定的真理和故事模式被人们所发现;而它们注定要不断重现。
上帝是天地万物的第一创造者,按照上帝的面貌创造出来的人类则是“第二创造者”,并通过他笔下的奇境来透视世界的真理,感到与自然融为一体。因此,神话、童话、传奇,都是真理的呈现方式,都是报送福音、传达喜悦的先知书的别种形式——就像他在《论童话故事》与诗作《神话创作》(Mythopoeia)中所表达的,托尔金的创作冲动已经超越了神话的民族性,而是着眼于极富宗教意味的普世价值。
可见,在重新审视基督教文化的过程中托尔金对幻想文学形成了全新的观点。这并不是说《魔戒》全书意在表达什么宗教教义,而无非是表明:整个“中土神话”是为全世界而写、献给所有人的一部童话。
【参考文献】
1、J.R.R.Tolkien, Tolkien On Fairy-stories, edited by Verlyn Flieger and Douglas A. Anderson, London: HarperCollinsPublishers. 2008.
2、Tony Kelly, Faith Seeking Fantasy: Tolkien on Fairy-Stories. Pacifica: Australasian Theological Studies, 2002, volume 15, issue 2.
3、Stuart D. Lee, A Companion to J.R.R.Tolkien. New Jersey: Wiley-Blackwell. 2014.
4、史敬轩《谁为佚者言——民族主义语境下的托尔金童话诗学》,《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2年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