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小说的“低徊趣味”
编者按:反映小城人生的小城小说是不同地域的具体小城之文学呈现,也是中华民族生活与文化的生动记录。学者张瑞英认为,中国现代小城小说是由系列短篇结构而成的散文体小说,这些小说组合成了“中国的日夜”。每一地域的小城小说,通过对该地域的定点透视,在表现种种生活场景及价值意义的基础上实现了对该地域及其民众的整体俯瞰与理性剖析。2020年12月,张瑞英专著《文化视阈下中国现代小城小说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经作者授权,中国作家网特遴选书中部分章节发布,以飨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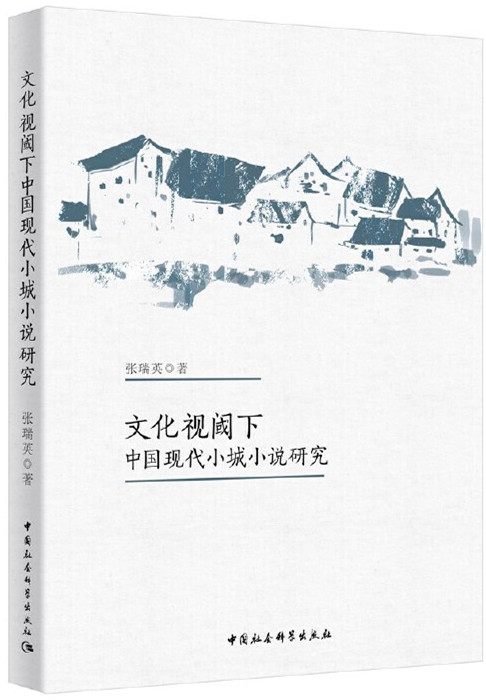
《文化视阈下中国现代小城小说研究》,张瑞英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12月出版
周作人对废名《莫须有先生传》的叙事特征有如此评价:“《莫须有先生》的文章的好处,似乎可以旧式批语评之曰,情生文,文生情。这好像是一道流水,大约总是向东朝宗于海,他流过的地方,凡有什么汊港湾曲,总得灌注潆洄一番,有什么岩石水草,总要披拂抚弄一下子才再往前去,这都不是他的行程的主脑,但除去了这些也就别无行程了。” 朱光潜在评废名的《桥》时说:“《桥》里充满的是诗境,是画境,是禅趣。每境自成一趣,可以离开前后所写境界而独立。它容易使人感觉到‘章与章之间无显然的联络贯串’。全书是一种风景画簿,翻开一页又是一页,前后的景与色调都大同小异,所以它也容易使人生单调之感,虽然它的内容实在是极丰富。” “单调”的景色之所以能感到其内容“极丰富”,全在于行程中对汊港湾曲的“灌注潆洄”和“披拂抚弄”。这种“低徊”的笔致趣味,会让作家笔下任何简单的物事都趣味横生,意义延展。鲁迅虽然批评废名的小说“只见其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之态” ,但他对废名文章的“好”其实是很明白的。鲁迅在日本时期很是欣赏夏目漱石作品的“低徊趣味”。他曾在与周作人一起翻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的附录中做了一篇《关于作者的说明》,文字简短,引用夏目漱石关于“低徊的趣味”的文字超过一半的篇幅,可见鲁迅对“低徊趣味”的欣赏和肯定:
他所主张的是所谓“低徊趣味”,又称“有余裕的文学”。一九〇八年高滨虚子的小说集《鸡头》出版,夏目替他作序,说明他们一派的态度:
“有余裕的小说,即如名字所示,不是急迫的小说,是避了非常这字的小说。如借用近来流行的文句,便是或人所谓触着不触着之中,不触着的这一种小说。……或人以为不触着者即非小说,但我主张不触着的小说不特与触着的小说同有存在的权利,而且也能收同等的成功。……世间很是广阔,在这广阔的世间,起居之法也有种种的不同:随缘临机的乐此种种起居即是余裕,观察之亦是余裕,或玩味之亦是余裕。有了这个余裕才得发生的事件以及对于这些事件的情绪,固亦依然是人生,是活泼泼地之人生也。”
“有余裕”是指态度从容,不慌不忙。这是鲁迅喜欢的,无论是文学,还是其他。鲁迅在1925年《忽然想到二》中也曾说过这样的话:
校着《苦闷的象征》的排印样本时,想到一些琐事——我于书的形式上有一种偏见,就是在书的开头和每个题目前后,总喜欢留些空白,所以付印的时候,一定明白地注明。……较好的中国书和西洋书,每本前后总有一两张空白的副页,上下的天地头也很宽。而近来中国的排印的新书则大抵没有副页,天地头又都很短,想要写上一点意见或者别的什么,也无地可容,翻开书来,满本是密密层层的黑字;加以油臭扑鼻,使人发生一种压迫和窘促之感,不特很少“读书之乐”,且觉得仿佛人生已没有“余裕”,“不留余地”了。
或者也许以这样的为质朴罢。但质朴是开始的“陋”,精力弥满,不惜物力的。现在的却是复归于陋,而质朴的精神已失,所以只能算窳败,算堕落,也就是常谈之所谓“因陋就简”。在这样“不留余地”空气的围绕里,人们的精神大抵要被挤小的。
外国的平易地讲述学术文艺的书,往往夹杂些闲话或笑谈,使文章增添活气,读者感到格外的兴趣,不易于疲倦。但中国的有些译本,却将这些删去,单留下艰难的讲学语,使他复近于教科书。这正如折花者,除尽枝叶,单留花朵,折花固然是折花,然而花枝的活气却灭尽了。人们到了失去余裕心,或不自觉地满抱了不留余地心时,这民族的将来恐怕可虑。
从书籍排版,到人的精神、人的心灵、人的生活,到外国学术著作的翻译,再到民族的将来,鲁迅一切都讲“余裕”,要留有余地,强调不要“失去余裕心”。
鲁迅在《三闲集》序言中曾谈到“三闲集”名字的来历:成仿吾以无产阶级之名指责鲁迅“有闲”,而且“有闲”还至于有三个 ,所以名为《三闲集》。这是鲁迅对成仿吾的回击,是趣谈,也是实情。回想鲁迅的“三闲集”、“二心集”、“而已集”、“南腔北调集”等等,从这些文集的名字可以想见,他实在不仅仅是个导师、战士,还是一个有趣洒脱之人。说他“有闲”,实在也不冤枉。鲁迅不仅喜欢闲暇的生活,还提倡闲暇的思维,喜欢有“有余裕”的艺术、物什。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欧战的时候,最重‘壕堑战’,战士伏在壕中,有时吸烟,也唱歌,打纸牌,喝酒,也在壕内开美术展览会,但有时忽向敌人开他几枪。” 他似乎喜欢这种带有游戏色彩的战斗场景。他在《读书杂谈》中指出,读书“就如游公园似的,随随便便去,因为随随便便,所以不吃力,因为不吃力,所以会觉得有趣” 。书籍排版要留有余地,这样才喜欢看,看得轻松舒服,才能看下去。印书、著书、读书、折花都要“有余裕”,道理是一样的。鲁迅由印书排版的留有余地,说到叙述文艺的书中的闲话笑谈带来的活气,直至说到一个民族的未来也要“有余裕心”。从上引夏目漱石的文字可以看出,“低徊趣味”正是对日常生活用心观察、体味的态度,这才是“活泼泼”的人生。鲁迅的文字似乎更多直面人生和社会现实的内容,风格也如匕首、投枪一般,但这并不妨碍他对“低徊趣味”的欣赏和肯定。鲁迅与废名、周作人的不同在于,他虽然也懂得欣赏这种“有余裕的文学”,但绝对不会局限于此。有学者认为,鲁迅与夏目漱石对“低徊趣味”的共同性认同,在于他们都经历了从“发现自我”到“超越封闭的自我”的思想变化过程 。鲁迅1935年对废名“只见其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之态”的批评,其实质不是否定“低徊趣味”本身,而是对其陷入“封闭自我”、沉溺于“低徊趣味”的不满。朱光潜在论述“所谓人生的艺术化就是人生的情趣化”时曾有这样一比:
阿尔皮斯山谷中有一条大汽车路,两旁景物极美,路上插着一个标语牌劝告游人说:“慢慢走,欣赏啊!”许多人在这车如流水马如龙的世界过活,恰如在阿尔皮斯山谷中乘汽车兜风,匆匆忙忙地急驰而过,无暇一回首流连风景,于是这丰富华丽的世界便成为了一个了无生趣的囚牢。这是一件多么可惋惜的事啊!
由以上引用、论述可以对“低徊趣味”有如下理解:所谓“低徊趣味”就如同旅游时在路上欣赏两旁的风景,生活的趣味就在两旁的绿草红花,鸟树蝶虫中。若只是直奔目的地,忘记了慢慢欣赏,“这丰富华丽的世界便成为了一个了无生趣的囚牢”。我们做任何事情总有一个主要目的,假如只是直奔目的而去,就没有了多彩的生活,而这种直奔主题的做法,往往达不到好的效果。再者,“低徊趣味”自然是“发现自我”、执着自我地感觉、体味方能得到,倘若拘泥于自我,而不是通过自我的感受、体味、认知大千世界,悲悯其他生命,就失去了“低徊趣味”的原意。
《呼兰河传》、《果园城记》、《边城》、《小城三月》等小城小说基本上都是小城作家回忆故乡的平常生活记录。这些小说没有核心人物,也不讲究情节,却能有“叙事诗”、“风土画”、“歌谣”的魅力。之所以有如此艺术效果,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叙述带来的“低徊趣味”。叙述是小说的基本方法,也是文体的重要特征。这里的叙述,不仅在于叙述的内容,更在于叙述的方式。小说叙述不仅在于展示自我,表达自己对生活的态度,还包括自己的生命观念和艺术观念,以及背后的思维方式及精神追求。低徊有情致的叙述方式,可以把一件简单的事情说得有滋味,可以将平常的事情说得有韵味。
翻开小城小说,会有一个普遍的感觉,小城没有特别主要的人,也没有特别重要的事,就是普通百姓的寻常日子。作者所选取的叙述方式,也几乎是完全按照时空及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一件事、一个人、一种场面,老老实实、按部就班地叙述。萧红的《呼兰河传》第一章,是对呼兰小城风貌的介绍。开篇叙述了呼兰小城的冷,接下去依次叙述呼兰小城的规模、特点、人物。小城最有名的要算十字街,十字街口集中了全城的精华,街上有金银首饰店、布庄、油盐店、茶庄、药店等各种店铺。城里除了十字街之外还有两条街,一个叫做东二道街,一个叫做西二道街。东二道街上有一家火磨、两家学堂,西二道街上有一家学堂。特别介绍了东二道街上的大泥坑及与大泥坑相关的故事。然后叙述东二道街上人的生活,染缸房里的人事,扎彩铺及扎彩的人。呼兰小城除了十字街、东二道街、西二道街外就是些个小胡同了。小胡同中有卖麻花的、卖凉粉的、卖豆腐的,他们依次出现后,就看到了天上的晚霞,然后一天就完了。春、夏、秋、冬,脱下单衣,换上棉衣,一年就完了。就对呼兰小城的传记式书写而言,这就是“阿尔皮斯山谷”中的汽车大路,真正美丽有趣的是路两旁的风景,这也是萧红平铺直叙中不时出现的情致化叙述。对呼兰小城的上述介绍或许是萧红第一章的任务,但她在叙述过程中写到每一处都如一道流水,在大方向不变的情况下,每流过一个地方,在“汊港湾曲”处,都“灌注潆洄”一下,什么“岩石水草”,都要“披拂抚弄”一下,如此叙述,则使小说不仅具有了“叙事诗”、“风土画”、“歌谣”的魅力,还让简单的故事拥有了丰富的内涵,小说具有了史诗的意义。
《呼兰河传》第一章,开篇就是具有画面感的“冷”:
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尺长的,一丈长的,还有好几丈长的,它们毫无方向的,便随时随地,只要严冬一到,大地就裂开口了。
严寒把大地冻裂了。
……人的手被冻裂了。
……水缸被冻裂了;
井被冻住了;
大风雪的夜里,竟会把人家的房子封住,睡了一夜,早晨起来,一推门,竟推不开门了。
萧红的叙述一点花招也没有,就那么直接、简单地引领读者去看东北寒冷的处处表现。虽然简单,却清新、生动。萧红笔下呼兰小城的“冷”,不仅有画面感,还极富生活情趣:
卖馒头的老头,背着木箱子,里边装着热馒头,太阳一出来,就在街上叫唤。他刚一从家里出来的时候,他走的快,他喊的声音也大。可是过不了一会,他的脚上挂了掌子了,在脚心上好像踏着一个鸡蛋似的,圆滚滚的。原来冰雪封满了他的脚底了。使他走起路来十分的不得力,若不是十分的加着小心,他就要跌倒了。就是这样,也还是跌倒的。跌倒了是不很好的,把馒头箱子跌翻了,馒头从箱底一个一个的跑了出来。旁边若有人看见,趁着这机会,趁着老头子倒下一时还爬不起来的时候,就拾了几个一边吃着就走了。他向着那走得不太远的吃他馒头的人说:
“好冷的天,地皮冻裂了,吞了我的馒头了。”
行路人听了这话都笑了。他背起箱子来再往前走,那脚下的冰溜,似乎是越结越高,使他越走越困难,于是背上出了汗,眼睛上了霜,胡子上的冰溜越挂越多,而且因为呼吸的关系,把破皮帽子的帽耳朵和帽前遮都挂了霜了。这老头越走越慢,担心受怕,颤颤惊惊,好像初次穿上了滑冰鞋,被朋友推上了溜冰场似的。
寒冷的天,一个老人冒着严寒去卖馒头,脚下有冰跌倒,馒头被路人抢去。这在启蒙话语中,完全是一幅落后贫穷的环境中民众受难图。可是在萧红写来,完全不是这种感觉。丢馒头、捡馒头、吃馒头、说笑话调侃、路人的笑,这一切虽然发生在天寒地冻中,却让人感到温馨快乐。在这里,萧红不是作为启蒙者俯视如此种种情境,而是作为百姓中的一员,感同身受地体味着他们的甘苦、达观和幽默。虽然生活不易,可日子就是这样过的,每个人在自己的职分上既努力生活,也追求、享受着简单的快乐。
东二道街南头卖豆芽的王寡妇儿子淹死了,“虽然她从此以后就疯了,但她到底还晓得卖豆芽菜,她仍还是静静的活着,虽然偶尔她的疯性发了,在大街上或是庙台上狂哭一场,但一哭过了之后,她还是平平静静的活着”。
至于邻人街坊们,或是过路的人看见了他在庙台上哭,也会引起一点恻隐之心来的,不过为时甚短罢了。
还有人们常常喜欢把一些不幸者归划在一起,比如疯子傻子之类,都一律去看待。
那个乡,那个县,那个村都有些个不幸者,瘸子啦,瞎子啦,疯子或是傻子。
呼兰河这城里,就有许多这一类的人。人们关于他们都似乎听得多,看得多,也就不以为奇了。偶尔在庙台上或是大门洞里不幸遇到了一个,刚想多少加一点恻隐之心在那人身上,但是一转念,人间这样的人多着哩!于是转过眼睛去,三步两步的就走过去了。即或有人停下来,也不过是那些毫没有记性的小孩子似的向那疯子投一个石子,或是做着把瞎子故意领到水沟里边去的事情。
王寡妇靠卖豆芽度日,因儿子淹死而疯了,但她依然知道得卖豆芽维持生计,人们同情她,但同情的时间很短暂,因为不幸的人太多,同情不过来。偶有小孩子恶作剧,加重着可怜者的艰难。萧红将这些事情一步步罗列下来,老老实实地讲述这些人之常事、常情。但读者在阅读这些文字的时候,王寡妇日子的艰难、愁苦,周围人的善良、无奈,不幸者的可怜、无助,小孩子的不懂事等等,都会历历在目,让人浮想联翩。这些简简单单如清风流水般的文字,清清楚楚地将呼兰小城的世事人情告诉了读者。作者将呼兰小城的形象、民风、民情、信仰、审美、衣食住行,连同神日鬼节的仙风鬼气一一道来,相比于大多数左翼作家面对乡村落后愚昧的单一性批判,萧红的《呼兰河传》多了一层欣赏与自省,不仅没有平淡之感,反而觉得既有个体的生动、形象,又有整体的协调一致,任何一种场景透视,都可推而广之到呼兰河,到中国,到全人类。萧红的文字当真是“汊港湾曲,总得灌注潆洄一番”,深入每个细微处,支流旁逸,水花朵朵,含义幽远。
又是一个春天来了,经萧红的“披拂抚弄”,春天的景色是那么多姿多彩,趣味横生:
三月的原野已经绿了,像地衣那样绿,透出在这里,那里。郊原上的草,是必须转折了好几个弯儿才能钻出地面的,草儿头上还顶着那胀破了种粒的壳,发出一寸多高的芽子,欣幸的钻出了土皮。放牛的孩子,在掀起了墙脚片下面的瓦片时,找到了一片草芽了,孩子们到家里告诉妈妈,说:“今天草芽出土了!”妈妈惊喜的说:“那一定是向阳的地方!”抢根菜的白色的圆石似的籽儿在地上滚着,野孩子一升一斗地在拾。蒲公英发芽了,羊咩咩地叫,乌鸦绕着杨树林子飞。天气一天暖似一天,日子一寸一寸的都有意思。
原野绿得那样随意自由,小草发芽那么曲折、有趣,春来的惊喜浮起在孩子和妈妈的对话中。野菜、野花、乌鸦、羊群,一切都充满生机,真个是“日子一寸一寸都有意思”。正是因为有秋的萧瑟,冬的寒冷,春天来得才如此令人欣喜,日子才会感觉一寸寸有意思。人生乐少苦多,少有的快乐会倍加珍惜。日子就在欣喜、悲哀中一点点前移;生命就在春夏秋冬中生老病死。——在这谁也改变不了的规律中,每一个人,甚至每一棵草也都在自己的职分上,在每一个生命节点作着自己的生存努力。这是每个生命的本分,也是每一个生命的光彩。
萧红笔下的后花园(《后花园》),因为园主并非怎样精细的人,多半变成菜园。
其余种花的部分也没有什么好花,比如马蛇菜、爬山虎、胭粉豆、小龙豆……这都是些草本植物,没有什么高贵的。到冬天就都埋在大雪里边,它们就都死去了。春天打扫干净了这个地盘,再重种起来。有的甚或不用下种,它就自己出来了,好比大菽茨,那就是每年也不用种,它就自己出来的。
它自己的种子,今年落在地上没有人去拾它,明年它就出来了;明年落了子,又没有人去采它,它就又自己出来了。
这样年年代代,这花园无处不长着大花。墙根上,花架边,人行道的两旁,有的竟长在倭瓜或黄瓜一块去了。那讨厌的倭瓜的丝曼竟缠绕在它的身上,缠得多了,把它拉倒了。
可是它就倒在地上仍旧开着花。
铲地的人一遇到它,总是把它拔了,可是越拉它越生得快,那第一班开过的花子落下,落在地上,不久它就生出新的来。所以铲也铲不尽,拔也拔不尽,简直成了一种讨厌的东西了。还有那些被倭瓜缠住了的,若想拔它,把倭瓜也拔掉了,所以只得让它横躺竖卧的在地上,也不能不开花。
长的非常之高,五六尺高,和玉蜀黍差不多一般高,比人还高了一点,红辣辣地开满了一片。
人们并不把它当做花看待,要折就折,要断就断,要连根拔也都随便。到这园子里来玩的孩子随便折了一堆去,女人折了插满了一头。
这花园从园主一直到来游园的人,没有一个人是爱护这花的。这些花从来不浇水,任着风吹,任着太阳晒,可是却越开越红,越开越旺盛,把园子煊耀得闪眼,把六月夸奖得和水滚着那么热。
胭粉豆、金荷叶、马蛇菜都开得像火一般。
其中尤其是马蛇菜,红得鲜明晃眼,红得它自己随时要破裂流下红色汁液来。
从磨坊看这园子,这园子更不知鲜明了多少倍,简直是金属的了,简直像在火里边烧着那么热烈。
可是磨坊里的磨倌是寂寞的。
后花园,半园菜,半园花。那半园寻常花草生长得随意简单,又恣意灿烂。它们不在乎“墙根上,花架边,人行道的两旁”,也不在乎雪埋风吹,随意扫个地盘种下甚至不用下种就能自己长出来,“年年代代,这花园无处不长着大花”,即使被倭瓜的丝蔓缠绕、甚至拉倒,在地上依然开花。被铲地的人铲了、拔了,越拔越多,“横躺竖卧的在地上,也不能不开花”。“这些花从来不浇水,任着风吹,任着太阳晒,可是却越开越红,越开越旺盛,把园子煊耀得闪眼,把六月夸奖得和水滚着那么热”。这半园如同施了魔法般的平凡花草,生命力强得几乎令人吃惊,感到不可思议,也令人敬畏。它们对这个世界的要求却简单得只有一点点,就能生长、开花,结果。没有人关注,也没有爱护,不管雨打风吹,哪怕缠绕铲拔,生命依然张扬,花开得恣意灿烂。这些看起来平凡甚至低贱的生命,其实是世界的主体。正是这些平凡的生命,装点着世界的华丽与悲戚。也正是那些如这些花草一样身份低微的小人物,真实而又执着地演绎着世上的悲喜哀乐,他们是生活素朴的底子。花园的花开得这么明艳、热闹,“可是磨坊里的磨倌是寂寞的”。几经曲折,数番低徊,反复渲染,原来萧红是用自然的盎然生机反衬人生的寂寞无聊,但同时也用“没有什么高贵”、却有着顽强生命力的野花来比拟磨倌的生命韧性。或许灰黯的磨倌与后花园明艳的鲜花外形上不能相比,但就其不屈不挠、韧性十足的生命强力而言,磨倌和明艳的花是一样的。这样老老实实、悲喜经心、低徊有趣、意义深远的叙述方式背后支撑的是萧红独有的生活观和文学观。
《呼兰河传》完成于1940年12月,正是民族危亡、救亡图存的时刻,大多数作家写革命、写战斗,萧红却在写着呼兰小城几个凡夫俗子普通烦琐的生活,写小团圆媳妇无辜的死,写月英凄惨的死,写金枝活着的艰难、屈辱,写怀孕生产的女人之痛苦无奈,写乱坟岗子毫无价值的死,一切生命没有价值没有尊严草木猪狗一样的生生死死。这不是一个理性作家的文学书写,而是一个善良敏锐的生命烛照与激情燃烧,她以其细腻聪慧、感同身受之心,捕捉着被时代大潮、响亮口号所遮蔽、忽略的各种生命委屈、无奈,将那些细小却持久的部分呈现于光亮处,让生命于宏大于琐碎之间得到一种整体展现。萧红就是这样,别人的写作是抛洒文采、技巧和传达思想,而她的写作是在燃烧生命,对于心中、笔下的一切,她太投入,太用心用情,全心全意,因此她能用最普通、最简单的手法把最平凡的事物写得生机勃勃,丰富多彩。在她那里,文学和生活是一体的。她在生命的朴实、真诚中发现趣味,寻找意义,也怀着对宗教一样的虔诚对待文学作品中的一切生命。
我们在前面曾经几次提到萧红说过这样的话:“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几种东西,一定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生活,有各式各样的作家,就有各式各样的小说。” 小说创作没有固定的模式,没有一定之规,它是随着生活的律动而改变着自己的节奏的。有什么样的生活就有什么样的作家,有什么样的作家就会创作出什么样的作品。汪曾祺也有类似的观点:“现代读者要求的是真实,想读的是生活,生活本身。现代读者不能容忍编造……现代小说的作者和读者之间的界线逐渐在泯除。作者和读者的地位是平等的。最好不要想到我写小说,你看。而是,咱们来谈谈生活。生活,是没有多少情节的。” 他还指出:“生活的样子,就是作品的样子。一种生活,只能有一种写法。”
萧红的创作忠实于自己的感觉,笔下丝丝流淌着她对于故乡的绵绵思绪,低徊宛转,铺叙延展。故乡是凝滞的,生活情境几乎是不变的,村中的山,山下的河,十年来没什么变化,大片的村庄生死轮回着和十年前一样。屋顶的麻雀仍旧是那样繁多,太阳也照样暖和,牧童唱的童谣依旧是十年前的老调。一天天,一年年,人们过着卑琐平凡的生活,天黑睡觉,天亮干活,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他们随着季节变化穿起棉衣、脱下冬衣。这样朴素平凡、亘古如斯的生活决定了萧红叙事方式的简单、朴实。倾情倾心的投入,对每个生活细节的“潆洄”、“披拂”,让简单、永久的生活拥有了生动的形象和深远的寓意。
呼兰河城里除了东、西二道街和十字街之外,就是些小胡同了,小胡同整天寂寂寞寞,间或有卖糖麻花、油麻花的。对此,萧红写来既温馨快意又淡远寂寥,真个如清新的风土画、凄婉的歌谣。其中对买麻花一出的描写,尤见萧红的观察能力和叙事水平。下面就让我们不厌其烦地将这个场景复述一遍:
间或有人掀开了筐子上盖着的那张布,好像要买似的,拿起一个来摸一摸是否还是热的。
摸完了也就放下了,卖麻花的也绝对的不生气。
于是又到第二家的门口去。
第二家的老太婆也是在闲着,于是就又伸出手来,打开筐子,摸了一回。
摸完了也是没有买。
于是,卖麻花的来到了第三家,家里是一个三十多岁女人,刚刚睡午觉起来,头顶上梳着一个发卷。女人一开门就很爽快,把门扇往两边一分就从门里闪了出来。紧随其后跟出来五个孩子,也都个个爽快,像一个小连队似的站成一排。
第一个是女孩子,十二三岁,伸出手来就拿了一个五吊钱一只的一竹筷子长的大麻花。她的眼光很迅捷,这麻花在这筐子里的确是最大的,而且就只有这一个。
第二个是男孩子,拿了一个两吊钱一只的。
第三个也是拿了个两吊钱一只的。也是个男孩子。
第四个看了看,没有办法,也只得拿了一个两吊钱的。也是个男孩子。
轮到第五个了,这个可分不出来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头是秃的,一只耳朵上挂着钳子,瘦得好像个干柳条,肚子可特别大。看样子也不过五岁。
一伸手,他的手就比其余的四个的都黑得更厉害,其余的四个,虽然他们的手也黑得够厉害的,但总还认得出来那是手,而不是别的什么,唯有他的手是连认也认不出来了,说是手呢!说是什么呢,说什么都行。完全起着黑的灰的,深的浅的,各种的云层。看上去,好像看隔山照似的,有无穷的趣味。
他就用这手在筐子里边挑选,几乎是每个都让他摸过了,不一会工夫,全个的筐子都让他翻遍了。本来这筐子虽大,麻花也并没有几只。除了一个顶大的之外,其余小的也不过十来只,经了他这一翻,可就完全遍了。弄了他满手是油,把那小黑手染得油亮油亮的,黑亮黑亮的。
而后他说:
“我要大的。”
于是就在门口打了起来。
五个孩子为了那个最大的麻花相互追逐、打斗,两个哥哥把姐姐扭住,最小的那个孩子想趁机捡点便宜抢到麻花,几次都没得手,落在后面嚎啕大哭。他们的母亲为了制止这场争夺战,只好拿来烧火的铁叉子奔过去,却不料失脚跌在院子中间的猪坑里,叉子也甩出去五尺远。
于是这场戏才算达到了高潮,看热闹的人没有不笑的,没有不称心愉快的。
就连那卖麻花的也看出神了,当那女人坐到泥坑中把泥花四边溅起来的时候,那卖麻花的差一点没把筐子掉了地下。他高兴极了,他早已经忘了他手里的筐子了。
至于那几个孩子,则早就不见了。
母亲好不容易把孩子们追回来,让他们在院子排起一小队在太阳下跪着,麻花一律解除。可这时孩子们手里的麻花或撞碎或差不多吃完了,只有第四个孩子手里的麻花没动,第五个孩子根本没拿到麻花。闹到最后,那女人硬是把第四个孩子手中的那根麻花退给了卖麻花的,付了三根麻花钱就把他赶走了。
为着麻花而下跪的五个孩子不提了。再说那一进胡同口就被挨家摸索过来的麻花,被提到另外的胡同里去,到底也卖掉了。
一个已经脱完了牙齿的老太太买了其中的一个,用纸裹着拿到屋子去了。她一边走着一边说:
“这麻花真干净,油亮亮的。”
而后招呼了她的小孩子,快来吧。
那卖麻花的人看了老太太很喜欢这麻花,于是就又说:
“是刚出锅的,还热忽着哩!”
在《呼兰河传》中,呼兰河城的气氛是灰暗的、阴沉的、憋闷的,但这段买卖麻花一段描写却别是一番情调,平添了不少乐子,让我们在忍俊不禁的同时,不得不佩服萧红的那“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在这段描写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满是童真的萧红,在饶有兴味地看着买麻花一家大小的闹剧,而且没有忽视任何一个小小的角色:姐姐尖锐的眼光,敏捷的动作;最小的孩子弱弱的样子,黑黑的手,挑来挑去的聪慧和贪心;兄弟姐妹的充满活力的争夺;母亲的“威风”、无奈、可笑和蛮横。还有其他只摸麻花而不买者的行为及行为背后的心思,卖麻花者的狡黠,等等。中间还穿插着五个孩子争夺最大麻花的打闹、孩子母亲跌到泥坑里的窘态等描写。最后写老太太买麻花及与卖麻花者的对话,无疑是这个买卖麻花场景中的点睛之处。就这么一个场景,让萧红细细写来,利落活泼,情趣盎然。可以想象,萧红是带着笑意在回忆中再次饶有兴味地观赏这一幕的。在她看来,这些孩子为了麻花的抢夺不唯是贫穷的日子让人贪吃忘节,而是写出了小城人日常生活的趣味和活力。在她笔下,豆腐蘸点酱好吃得让没吃过的人不能想象;为能自由随便地吃豆腐,一个孩子的愿望是长大开豆腐坊。还有这样的家长,为了吃一块豆腐,竟豁上说:“不过了,买一块豆腐吃去!” 在萧红幼年的记忆中,这都是人生的趣味和奢侈,当她写到这些时自有其发自内心的喜爱与眷恋。在萧红眼中,贫穷、乏味的日子也布满了一个个有趣的细节和场景。世界在在那个顽皮好奇、对世界充满兴趣的女孩眼中是可爱有趣、意味隽永的。同时,女孩的眼中也混合了成年萧红的睿智和深刻,于是在一切天真自然的事象背后又有冷峻的审视,我们也就在她那看似平铺直叙甚至稍逊文采、略显稚嫩的文字中体会一个故乡回望者那敏感而复杂的情怀。在《呼兰河传》中,萧红的视角是天真的,也是成熟的;她所看到的世界是热闹的,也是荒凉的;她所描述的生活是琐碎的,也是深刻的;她所运用的叙事模式是简单的,也是灵活的,富于变化的。——深入理解的关键在于透过现象看本质!所以,赵园曾说:“萧红写‘生’与‘死’,写生命的被漠视,同时写生命的顽强。萧红是寂寞的,却也正是这寂寞的心,最能由人类生活也由大自然中领略生命感呢!一片天真地表达对于生命、对于生存的欣悦——其中也寓有作者本人对于‘生’的无限眷恋的,正是这个善写‘人生荒凉’的萧红,而由两面的结合中,才更见出萧红的深刻。”
(注释已略去,详见原书文章。)
作者简介:张瑞英(1965-),山东高密人,文学博士,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文化视阈中的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小城镇小说以及莫言小说等。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丛刊》《鲁迅研究月刊》《文史哲》等发表论文数十篇;已出版《地域文化与现代乡土小说生命主题》《文化视阈下中国现代小城小说研究》等专著;主持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及省部级社科项目多项;研究成果获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二等奖项多次。
- 1957年,萧红“回家”[2021-12-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