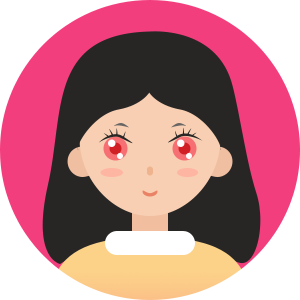湖畔诗社的年轻人
四个年轻人做梦也没有想到,一九二二年的那个春天,波澜不惊的西湖边,因他们的即兴发挥,湖畔诗社——竟然成为中国新诗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存在。一百年来,湖畔诗社作为一家文学社团被人们不断提及,湖畔诗社的年轻人和他们的诗作时常走进课堂,走进读者的心里。一代一代的读者,常常为四个年轻人在西湖边的举动所感动。因为他们是用自己的心血和天性纯情来滋养读者的心灵,滋养新诗和中国文学。
文学的历史,是有许多杂质的,不少作品距离人性很远,从中看不到关于人的半点影子,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只在文字游戏中浪费生命;有的文学作品中,不仅看不到人性的影子,也看不到真实时代的影子,仅凭借声东击西耍一些文字滑头,在历史和现实的魔幻里,成为读者需要猜测的谜语。所以,看到真性情的文字,仿佛听到天籁一般,在人们心里掀起阵阵漪涟,令人久久难以忘怀。
一
一九二二年杭州的春天,和往年一样,西湖边的柳树,在春风里摇摆了几下,柳条就露出一点点黄茸茸的柳芽,在西湖边享受阳光和软软的春风;从宝石山上飞下来的燕子,贴着西湖的水面翱翔,轻盈而欢快。杭州的山色,已经慢慢呈现青绿,和春天的阳光融为一体,显得格外柔和、温润。应修人、潘漠华、冯雪峰、汪静之四位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在游览了西湖的湖光山色之后,应修人提议,一九二二年四月四日,在中国杭州孤山上西泠印社的四照阁里,成立一个诗社!这就是后来名扬天下的湖畔诗社。四个年轻人不经意的举动,冥冥中已经惊动了中国新文学的历史,在中国新诗史上留下灿烂的一笔。
关于湖畔诗社的起因,冯雪峰回忆:“1921年,当时在杭州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汪静之已经有诗作在刊物上发表,这引起了那时也正在热心于新诗写作的应修人的注意。……大约在1922年初他开始同静之通信,接着由静之介绍也就和漠华和我通信,那时漠华和我也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读书。1922年3月底……(修人)就来杭州同我们一起在西湖各处游玩了一个星期……由他发动,主要的也是由他编选,从我们四个人习作的诗稿里挑出一些诗来,编成一集,名为‘湖畔’,以作我们这次会晤的纪念……由修人出资自印,于4月间出版了……我们之间的友谊却也有进无退……从此以后,我们各人之间的友谊是仍然不变的。”(冯雪峰《应修人潘漠华选集·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
冯雪峰是当事人,三十多年后的回忆,大抵是准确的。汪静之回忆,当时他的诗已经编在《蕙的风》里面,冯雪峰他们认为,四个人选编了三个人的诗,不合适,于是从汪静之的《蕙的风》里抽出四首诗,编在《湖畔》里,这样,四个年轻人的作品就完整了。当年的惊世骇俗烟消云散之后,一切归于平淡,当事人回忆起来,仿佛在说别人的故事。当年《湖畔》一经出版,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四个年轻诗人在卫道者的一片毒骂中,十分惶恐,幸亏有鲁迅、周作人、胡适等新文学名人的支持肯定,才让他们的诗心不灭,为中国新诗史上留下一缕新风。
当年四位年轻人正是二十岁左右的青春年华,杭州的湖光山色和五四及新文化运动的天然融合,焕发出奇异的光芒,让这些年轻人的情感、思想一起迸发。有意思的是,四位《湖畔》爱情诗人都是男性,他们有发自内心对女性的好奇和渴望,天然的身体和自由的思想,所以他们笔下的爱情诗,自然天真、清新幼稚,如刚刚出土的幼苗,鲜嫩得没有半点杂质。但是,这幼苗又是从泥土中生长出来的。汪静之的《过伊家门外》,只有短短三句,却写出了一个年轻人内心的波涛汹涌:“我冒犯了人们的指摘,/一步一回头地瞟我意中人;/我怎样欣慰而胆寒呵。”
二
今天的人们读湖畔诗社的爱情诗,喜欢这些爱情诗,是因为这些爱情诗,都是年轻人自己真实生活的抒写。没有经历过真正爱情的所谓爱情诗,大多是无病呻吟,湖畔诗社的年轻人写的爱情诗,几乎每一首诗都是来自他们生活中的故事。
湖畔诗社的四个年轻人中,汪静之在杭州时间最长,他的爱情诗写得最多,他的爱情故事也最生动。他小时候由父母指腹为婚,后来和对象以及对象的姑姑曹珮声,像兄弟姐妹一样,三个人青梅竹马,整天在一起玩。但是,渐渐长大的汪静之,其指腹为婚的对象忽然在十二岁时去世了,而曹珮声已经出落成风姿绰约的大姑娘。汪静之情窦初开,喜欢上了曹珮声,却遭到曹珮声的一声断喝:“你疯啦!我是你姑姑!”汪静之一下子没有了勇气。后来,曹珮声在老家出嫁,再后来到杭州读书,寻找自己的世界,并考取杭州女子师范学校。汪静之也到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
远离家乡的曹珮声知道,汪静之内心依然钟情于她,只不过碍于这种世俗关系,才没有跨出这一步。曹珮声关心汪静之的情感生活,希望有一个称心如意的女子,成为汪静之的终身伴侣。在风景如画的西湖边,曹珮声去看望汪静之,每次去,都自作主张带一个女同学一起。私心目的,就是要把自己的同学介绍给汪静之——让他认识认识这些才貌双全的女同学。曹珮声也是一位才貌双全的女性,据说还是个学霸,所以在同学中威望很高,女同学都愿意随她到西湖边玩。曹珮声前前后后一共带了八个女同学,结果她们都不大愿意搭理汪静之。这让汪静之十分无奈,他当时写道:“最初相见惊心艳/一见顿时魂尽销/无奈美人不理我/心凉半截觉无聊。”还写道:“美女无情冷若冰/不敢心萌爱慕情/眼内寒冰挡爱意/冷面冷颜我冷心。”
后来,汪静之看中了一位在杭州女子师范读书的姑娘符竹因,于是不管不顾,用徽州人的执着,猛烈追求。汪静之不善言辞,便用写信、写情诗的方式追求符竹因。据说,汪静之当时给符竹因写情书,最多的时候,一天寄出十三封信,这恐怕在中国情书史上也不多见吧!
符竹因出生于临平的一个小康之家,平时在学校里的形象是中规中矩的好学生,突然一天收到十三封信,引起学校训育主任的注意,一查,原来好学生符竹因在外面谈恋爱。学校打算开除她,或者让她退学。但因为符竹因品学兼优,许多老师都不忍心惩罚她,最后决定给她诫勉谈话。学校还把此事告诉了符竹因的父亲。好在符竹因的父亲比较开明,也有新思想,他了解情况以后,竟然同意女儿的选择,让汪静之在睡梦中笑醒。
有这样爱情生活的诗人写的爱情诗,自然吸引人。湖畔诗社诗人们的爱情诗,是发自内心的自然流露,没有矫揉造作,更没有无病呻吟,他们的爱情诗,每一句都是真实的情话。正如《湖畔》扉页上的题词:“我们歌笑在湖畔,我们歌哭在湖畔。”所以,他们的诗,有时候是童言无忌,他们把内心的情感赤裸裸地、不加掩饰地呈献给读者,尤其随着第二本冯雪峰、应修人、潘漠华的诗集《春的歌集》的出版,再加上汪静之《蕙的风》的出版,湖畔诗社的名声日益扩大。
三
其实,湖畔诗社的爱情吟唱,坚持一直唱下去的,只有汪静之一个人。汪静之唱到晚年,唱到最后,湖畔诗社成为一个人的湖畔诗社。当年意气风发的四个年轻人中,宁波人应修人一九二五年到了上海,参加五卅运动,在革命的洪流中秘密加入共产党,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一九三一年到中央组织部工作,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四日牺牲,成为湖畔诗社的第一位革命烈士;金华武义县的潘漠华,离开西湖以后,到北京大学读书,一九二六年参加北伐战争,在革命低谷时,加入共产党,之后在浙江、上海、河南、河北等地从事教育工作,同时秘密进行地下革命工作,一九三三年十二月被捕,次年牺牲在国民党监狱里。
新诗人有理想、有信仰,从诗人到革命家,无怨无悔。还有宁海县的柔石,他也是湖畔诗社的成员,年纪轻轻,也牺牲了。汪静之曾经感叹,五四运动以后写新诗的人中,有六个烈士,其中湖畔诗社占了一半。冯雪峰此后的经历十分坎坷,他曾经到北京大学旁听,后来在上海从事左翼文化活动,还去过中央苏区,担任过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参加过红军长征,后来党中央又派他到上海,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不久被捕,关进上饶集中营,被营救释放后,到桂林、重庆从事文化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冯雪峰在上海华东军政委员会和上海市文化艺术界联合会担任领导职务,后来到北京,在中国作家协会、《文艺报》等单位担任领导,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
汪静之早年得到鲁迅、胡适、周作人等名流的关照,爱情诗创作得心应手,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一部接一部地写出来。新中国成立以后,老朋友冯雪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当领导,于是邀请汪静之北上,到出版社做编辑工作。后来情况变化了,汪静之的日子并不好过。一九七六年以后,汪静之又在西湖边生活了二十年,他送走了当年一天给她写过十三封信的爱妻符竹因,重新恢复了湖畔诗社,建立了湖畔诗社纪念馆,将湖畔诗社的精神传承给后人。
四
湖畔诗社已经百年,但是那种脱俗一样的清新、天籁般的幼稚,自然质朴的爱情诗,依然在人间流传。当年汪静之望着年纪相仿的姑姑曹珮声的照片,写下了自己的相思:“我看着你,/你看着我,/四个眼睛两条视线。/整整对了半天,/你也无语,/我也无言。”如此相思,如此表达,清纯到了极致。再如《伊底眼》:“伊底眼是解结的剪刀;/不然,何以伊一瞧着我,/我被镣铐的灵魂就自由了呢?”这样的比喻,直抵人的心灵。
当年许多名流为湖畔诗社的爱情诗撑腰打气。周作人说过:“他们的是青年人的诗,许多事物映在他们的眼里,往往结成新鲜的印象……过了三十岁的人所承受不到的新的感觉,在诗里流露出来。”朱自清读了《蕙的风》以后,说:“小孩子天真烂漫,少经人世间底波折,自然只有‘无关拦’的热情弥满在他的胸怀里,所以他的诗多是赞颂自然,咏歌恋爱,所赞颂的又只是清新、美丽的自然,而非神秘、伟大的自然;所咏歌的又只是质直、单纯的恋爱,而非缠绵、委曲的恋爱。这才是孩子们洁白的心声,坦率的少年气度,而表现法的简单,明了,少宏深、幽渺之致,也正显出作者底本色。他不用锤炼底功夫,所以无那精细的艺术,但若有了那精细的艺术,他还能保留孩子底心情么?”朱自清先生的看法,是很有见地的。当时朱自清是湖畔诗社热心的扶持者,他后来还说:“专心致志做情诗的,是‘湖畔’的四个年轻人。他们那时候差不多可以说生活在诗里。潘漠华氏最凄苦,不胜掩抑之致;冯雪峰氏明快多了,笑中可也有泪;汪静之氏一味天真的稚气;应修人氏却嫌味儿淡些。”朱自清毕竟是文学鉴赏大家,对湖畔诗社的诗人作品,自有独到的看法。宗白华先生当时也对汪静之的爱情诗给予充分肯定,认为汪静之是“一个很难得的,没有受过时代的烦闷,社会的老气的天真青年”。在宗白华看来,汪静之《蕙的风》里的诗,是“如同鸟的鸣,花的开,泉水的流”一样的“天然流露的诗”。
湖畔诗社已过百年,蓬蓬勃勃、如火如荼的爱情诗时代仿佛渐行渐远,杭州西湖边的湖畔诗社遗韵,何时在西湖边桃红柳绿时再来?一百年?两百年?难说。但是,相信三百年以后,还会有人说起洋溢着真情实感的湖畔诗人的诗作!
 更多
更多

罗振亚:关于当下诗歌现状与未来的对话
“中华传统文化对新世纪诗歌构成的是精神思想和艺术技巧的综合性辐射,对当下诗歌具有正面价值的引发和渗透。我们真应该静下心来,细致考辨其间的运作规律。”
 更多
更多

柴德赓与刘乃和:亦师亦友三十载
《柴德赓日记》中师友、同事人名出现最多的是陈垣,其次是刘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