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写作如同盖房子,用新砖瓦还是老石料,是建筑者的趣味,但都是为了现实的居住和应用。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要找到大的方向,要用自己的腿脚走路。 穆涛:用自己的腿脚走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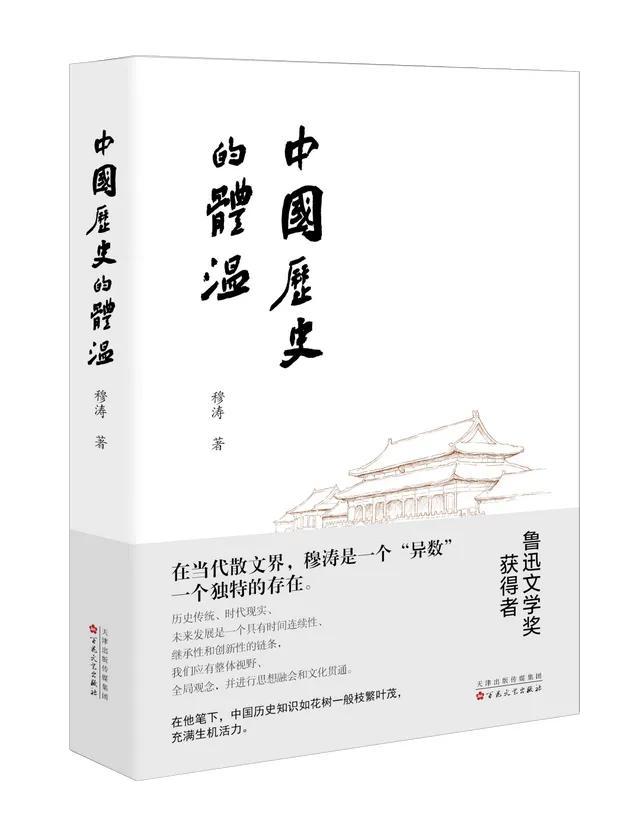
《中国历史的体温》,穆涛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23年1月出版,58.00元
2014年,《美文》杂志常务副主编、散文家穆涛《先前的风气》获得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有媒体请穆涛说感言,他只说了一句话:“平凹主编让我做编辑,还主持常务工作,我却得了创作的奖。让我当裁缝,我却织布去了。”
他真是这么想的,觉着是“不务正业”。实际上,他在兢兢业业推举《美文》“大散文”旗帜的同时,也利用碎片时间写了不少文章。一直到2022年,穆涛整理了一批读史札记,其中多是两三万字的长文章,发表在《江南》《大家》《作家》《人民文学》等杂志上。有朋友说穆涛“井喷”,他却说,其实是收拾老房子,把多年积攒下来的东西,选一些耿耿于怀的擦了擦灰尘,让其发出本来的光亮。他把这些文章依照时间顺序和写作思路分别整理,这样,又有了《中国人的大局观》和《中国历史的体温》这两本书。
中华读书报:《中国人的大局观》是您几十年读书思考的积累,这部作品的创作契机是什么?
穆涛:我不是作家,是编辑。我下功夫读了一点汉代和汉代之前的书,不是为了写作,是编辑杂志的需要。1998年我担任《美文》副主编,平凹主编倡导“大散文”写作,我要配合他的思路,并在《美文》具体编刊中呈现出来。“大散文”不是指文章的长短,而是指审美的格局和气象。在沟通中他建议我多读一些汉代的文章,这之前我比较喜欢韩愈,后来我从汉代的陆贾、贾谊、晁错、董仲舒开始读起,继而又系统读了《史记》《汉书》《淮南子》《礼记》,渐渐沉浸其中。
中华读书报:这部书历史知识丰厚,您是用做学问的功夫去写作。
穆涛:我不是刻意准备去写这本书的。河北廊坊有一句土话挺形象,叫做“搂草打兔子”,本来是去拔草的,顺手打了一只兔子。我读书有一个笨习惯,说是做笔记,其实就是抄书。这也是逼出来的,尤其是史书,没有时间专门研读,工作中杂事多,有空了就抄几段,事情忙了就放下。我个人的经验是,抄书好,抄一遍等于读三遍。作家写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要留心一个重要问题——中国的史书体例很特别,写一个人物,仅仅读他的传是不够的,会挂一漏万。
中华读书报:写作《中国人的大局观》和《中国历史的体温》两部书时,是怎样的状态,散文写作是否也需要丰沛的想象?
穆涛:历史是活的,是有生命的。历史不是老掉了的牙,不是物化了树根,也不是失去活力的根雕,摆在展览厅里由我们说三道四。树根成为根雕之后,就不再是树根了。读史书,像穿越回到了旧时光里,也像来到一条大河的水源地,一切都是陌生而新鲜的,我只是把我看见的记述下来,是见到的,不是想象出来的。
中华读书报:《中国历史的体温》是一部有温度、有性情的作品,其中也有很多辩证的思考,您是怎样去“参悟”的?
穆涛:我不是参悟,是瞎琢磨。比如,我们今天处于改革的年代,所谓改革,就是旧有的东西,不适合新环境了,需要改变。但改变的同时,还要弄清楚应该坚守什么,不是什么都改,不是在所有的领域全部重置炉灶。应该找到与中国优秀传统相衔接的接口。用大历史的眼光看,尽管很多东西都在变化,但自古至今,有三个层面的东西没有变。一是空间大环境没有变,太阳还是那个太阳,月亮还是那个月亮,星辰仍旧,地球带着月亮围绕太阳旋转的规律依旧。二是山川海洋与大江大河的走向基本没变。三是人性中最基本的东西没有变,也不会变,孝敬父母,养育儿孙,这些东西不会变的。今天的作家,外国的文学名著看得多,这是开眼界的好事。但要留心两个细节:邻居家的大树,是在人家土地里长起来的。看明白一棵树,只看树冠是不够的,还得弄清楚树根下面的东西。如果把这棵树移植过来,要转换制式。文学不是数学、物理、化学这样的自然学科,是社会学。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要找到大的方向,要用自己的腿脚走路。
中华读书报:《中国历史的体温》中有一篇《念旧的水准》,提出“读书治史不是念旧,旨在维新”,这是在特别强调什么?
穆涛:写历史题材的文章,今天称为“历史散文”,这个命名应该推敲的。文学写作如同盖房子,用新砖瓦还是老石料,是建筑者的趣味,但都是为了现实的居住和应用。一个人穿了汉代的衣服,不是想回到汉代,也回不去。历史题材的写作,是给自己盖房子,不要弄成仿古建筑,去掉装模作样为宜。
中华读书报:《长安城散步》是一组短文章,隽永精致,耐人寻味。在《关于朴素》中,您说“朴素不是修养,是骨头里的东西,是气质”,这怎么理解?
穆涛:穷日子里的苦,不是朴素,是简陋,是生活中的无奈。富人低调做事,也不是朴素,是修养,是潜于心底的一种奢华。朴素真真切切,却是高大上的。朴素是天生丽质,不是人工可以维护的,是骨头里的气质,不分高低尊卑。
中华读书报:作为贾平凹的同事和朋友,您和他多有合作,比如2012年出版的《看左手》,十年后又有《明日在往事中》,您愿意评价一下他的画吗?
穆涛:用苏轼画论中的一个观点,可以映照平凹主编的画,“世之工人,或能曲尽其形,而至于其理,非高人逸才不能辨”。他作画,“虽无常形,而有常理”,更多的是臻于妙理。生活里他是宽厚的儒者,忘知守本,作起画来是自我放逐弃了楼观的道人,异想天开,想起一出是一出。他的画,是灵魂出窍的,身子在五楼,念头或思想在九楼的窗口跟你打招呼。他的画,是从山不是山,水不是水,走向山更不是山,水更不是水。从山水呈现着什么,到山水征兆着什么。
中华读书报:您的文章重趣味,善用典,节制,内敛,往往小中见大,绵里藏针。比如《先前的风气》,内容涉及经史春秋,历法农事,帝皇将相,文情书画,饮食男女,除了少数篇幅,大多仅为寥寥数百字或千余字,却语尽而意不尽。这样的风格,是逐渐形成的吗?
穆涛:《先前的风气》中的文章,基本是《美文》杂志每期扉页上的导读语,只有一页纸的地方,字数有限制,想多写也不行。这个栏目,以前是平凹主编写,读者很爱看。他写得好,编辑部琐碎的稀松平常事,也写得神采飞扬。有一天他把我叫到办公室,说这一段事情多,让我替他写几期。我说这是主编的活,我干不了。他问我:“知道做副主编最重要的是什么吗?”我说:“听主编的话。”他说:“回答正确,写吧。”从1999年开始,就这么写下来了。平凹主编写的叫“读稿人语”,我写的叫“稿边笔记”。扉页上的这些话,写起来挺费劲的。要体现编者的用意,又不能太具体。大散文是什么? 散文写作应该“大”在什么地方? 这些东西是不能喊口号的。我从中国古代文章的多样写法入手,再参照史料,尽可能地去掉书袋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