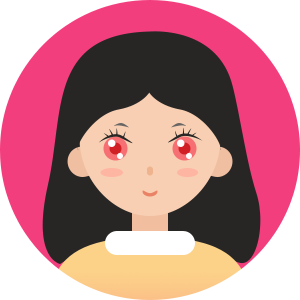新晋鲁奖获得者多年来一直研究女性文学 张莉:让看不见的看见 让听不见的听见
近日,文学评论家、女性文学好书榜发起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莉主持选编的《暮色与跳舞熊:2022年中国女性文学作品选》出版面世,书中首次纳入非虚构作品,这些作者跨越“50后”到“90后”,她们的作品展现出丰富、深刻的女性命运。
张莉2022年8月凭借《小说风景》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时隔12年,成为继赵园老师之后,又一位获得鲁奖的女性批评家。作为文学院教授,张莉一直活跃在当下的文学现场和教学一线,她开设的《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研究》线上慕课(大型开放在线课程)、《张莉的女性文学课》音频课,受到同学们欢迎。自2019年以来,张莉带领她的研究生团队推出“女性文学作品年选”,随后,又发起“持微火者·女性文学好书榜”,为普通女性尤其是年轻一代女性提供了从自由写作到走向文学殿堂的更多可能性。
今年3月的一天,张莉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的独家专访,畅谈她近些年与女性文学研究相关的那些事儿。张莉说:“女性文学研究追求的是平等,我希望更多的普通女性拿起笔写作。”
将文学品味和女性精神合在一起,让更多读者看到有意义的女性文学作品
北青报:请谈谈您选编女性文学年选以及创立女性文学好书榜的缘起是什么?
张莉:2004年,我来到北师大,跟随王富仁先生攻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当时我的博士论文选题是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也是我的女性文学研究之路的起点。2018年6月我调到北师大文学院教书,9月,对137位当代文学现场最活跃的作家发起了“我们时代的性别观”田野调查,那次调查也成为当年有影响力的文学事件。
为什么要做女性文学年选呢?其实是想弥补一个遗憾,做博士论文时我发现,早期女作家们发表的作品只能在零散的一些资料里看到,就萌生了做一本女性文学年选的念头。后来,我和我的研究生团队一起动手编撰《2019、2020、2021年女性文学选》,主编了《新女性写作专辑:美发生着变化》。在这个过程中,我开始意识到那些新近出版的女性文学作品,在我们当下的文学生活中非常重要。因此,从2021年开始,我开设了公众号“女性文学工作室”,发起了“持微火者·女性文学好书榜”,带领研究生团队一起阅读、推荐女性文学作品,关注与女性话题、女性命运、女性生存相关的内容。
作为一个当代文学现场的老师,我认为了解读者的阅读趣味和图书出版动态非常重要,可以拓展我的研究视野。当代文学研究者应该要有在场感。这种在场感不仅仅包括参加作品分享会,还应该包括要了解当下文学发生过什么、正在发生什么,以及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做榜单、做年选的工作都是对我们学术方向的一个促进。
我们做女性文学书单是关注我们时代的女性文学、女性生活和女性生存,希望以此记录时代女性精神、女性气质的变迁。而做年选,则是把散落在文学杂志的优秀文学作品推荐给大家,也包括关注新晋的青年女作家。我希望一方面能推动中国女性文学、当代女性文学的发展,另外一方面通过有趣味的引导,让更多读者看到那些有意义的女性话题作品。
关注作家是否是用文学的方式去传达女性视角、女性精神和女性立场
北青报:“持微火者·女性文学好书榜”的评选方法是什么?在您看来,这个书榜有什么不一样的?
张莉:我们榜单分春、夏、秋、冬四个书单,每隔三个月发布一次,我和团队阅读该季度文学现场出现的女性作家作品,反复讨论并写下推荐语。次年2月,女性文学工作室推出女性文学好书榜年榜。
关于这个榜单,我更强调它的文学性。更关注作家是否是用文学的方式去传达女性视角、女性精神和女性立场。评选工作由我和我的研究生团队共同完成,他们中有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也有几位本科生;研究生中有当代文学研究专业,也有文学创作与批评专业,也就是说,他们有的是研究者角度,有的是创作者角度,角度和侧重点也不一样。
对榜单的每一本书,他们都会做非常认真的准备,对于上榜的书,也都会认真阅读,讨论的时候,会把所有书都放在桌子上,大部分同学都说这本书好,都投票给它,它才可以上榜。我们基本要求团队面对面交流,每次我都会在现场,经常会从下午2点一直讨论到晚上七八点。会有很多出版社寄书给女性文学工作室,但也有很多书是同学自己去发现的,这个榜单凸显的是青年人的阅读视野和文学趣味。
有许多影视公司会通过我们的书单去找这些作者或者作品。姚鄂梅的《家庭生活》刚出版,同学就注意到了。责编告诉我们,女性文学好书榜是这本书上的第一个榜单。
如果作品写得没那么好,我们把它推出来,榜单的趣味、信任度就会打折扣。所以,我们要对得起读者的信任,真心觉得好再推荐。
做女性文学好书榜的初衷,当然是为读者推荐好作家、推荐好作品,对于作为教师的我来讲,还希望通过这样的工作去培育人、培养年轻人的文学品味和阅读视野。
女性文学好书榜有一个板块是推荐世界各国的女性文学作品,这是有意为之,我也希望这个榜单能代表青年一代读者对世界文学的关照和审美判断。要引领年轻人思考,在世界文学的视野之下,中国女作家们在写什么,国外的女作家在写什么。在这样的文学视野观照下,他们会思考中国女性文学未来的发展在哪里、独特性在哪里。
北青报:您如何把握年轻人的评判基准,平时教学中有哪些比较深的体会?
张莉:我说过,最美好的师生关系是教学相长,互相激发。理想的课堂应该是敞开的。我喜欢和同学们讨论问题,这个讨论对我也是受益的。当然,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也获得了成长,有些成为文学现场的青年批评家,有些则开始进行文学创作并且发表了文学作品。另外,我也获得了和学生在一起用新奇的目光打量文学的经验。有很多书是我在他们推荐下阅读的,比如《暮色将近》,我希望我们能达成一种审美信任的关系。
当从来没有专业写作经验的女性开始记下自我的生活,那本身就深具意义
北青报:从第一本女性文学年选问世到今天,《暮色与跳舞熊:2022年女性文学作品选》已经是第四年,在您看来,做年选经历了哪些变与不变?
张莉:四年前,我开始担任年选主编,我们不仅做女性作品年选,还有短篇小说20家和当代散文20家,这三个年选其实是一个工作团队,主要由我的硕士研究生组成,当然,他们中大多数人是从研一研二来参与这个工作,研三就会退出。所以,团队成员是流动的。虽然三个年选是一个团队,但同学们各自侧重的方向不同,也会在阅读杂志过程中互相推荐,避免遗漏。
年选不是在年终最后的时候才收集作品,而是每天都有意识地去阅读或者关注当下文学作品,要培养在场感。谁是新晋作家,作家的这部作品是否有代表性,要形成判断,需要持续关注和体会,才能最终形成自己的尺度。
编选的团队大概有六位同学参与,我们经常讨论,他们会告诉我喜欢哪位作家、哪部新作品。年选篇目我们会投票决定,大部分我们都有共识,但也有三到四部作品有不同意见,这个时候纠结得最久。当然,我有一两部的决定权。有一次,讨论女性文学年选,一位同学说:“老师我还是觉得这个作家的写作手法太传统,妈妈那辈才会看。”我说:“你这句话说得多好啊,我们的读者群不仅仅有年轻人,还有很多妈妈啊,这就是把它选进来的理由。”这样一说他们就懂了,我的意思是,我们虽然侧重年轻读者,但也追求读者群体的广泛性,也希望阅读趣味多元性,不能以一个人的好恶为判断尺度。
北青报:您一再强调文学的气质、推出新人,这也是做年选的价值所在吧?
张莉:从2022年开始,“女性文学年选”所收录的20个故事打破了题材的分野,既有虚构作品,也有非虚构作品。把阿依努尔的非虚构作品《单身母亲日记》纳入,让年选构筑的女性写作版图更为开阔和完整。年选每年都会推出新的女作家及其作品,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所在。今年我们特别推荐的是杨知寒,还有阿依努尔,她们都是“90后”作家。
我的一位研究生曾经告诉我,她在美甲店里看到了一本翻破了的《2019年女性文学选》,那个场景真让我开心。作为编者,我希望年选能越来越深入地走进普通读者的生活中去,这本女性文学年选其实就是希望和普通读者在一起,一起阅读这一年度中国女性的故事和生活。同时我也希望普通读者在未来能加入到写作者的行列,写下她们的所见、所闻、所想。
事实上,近年出版的非虚构女性作品中,无论是《秋园》还是《日日杂记》都告诉我们,当从来没有专业写作经验的女性开始记下自我的生活,本身就深具意义。今天,对于一位女性而言,在写作中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写出所见所闻,其实就是在自我解放,是在对自我进行确认。
强调女性视角重要的同时,也希望强调女性所写题材的普遍性,强调人类书写主题的共通
北青报:就您的感受来说,这些年出版的趣味以及阅读趣味发生了哪些变化?
张莉:最近一年多来,“女性文学工作室”总是收到许多有关女性话题的书。阅读过程中我们团队慢慢意识到,有一些书只是徒有其名;有一些书则经过口口相传,很有口碑;还有一些书营销做得不好,但其实写得很好。我们愿意推那些没有被注意到,但的确很有品质的书。好的作品要有好的回报,好的劳动要有好的回报。这是我们的工作宗旨,我们要给好书以好的回馈,写下诚恳的评价,也会尽力推荐。当然,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大家也在学习,向那些写出好内容的作者学习。
北青报:我看到年选里一直保持“爱、秘密和远方”的栏目,这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张莉:最初做女性文学作品年选时,我希望它能给读者耳目一新的感觉,耳目一新不仅仅包括内容、设计、主题,也包括不使用一些刻板化词语,比如说,一翻开女性文学作品可能大家总会想到“爱情、婚姻、家庭”这些词。但我不使用它们,我使用的是“爱、秘密和远方”,我用这三个词对女性写作进行分类。无论是爱,还是秘密或远方,这三个词语都具有普遍性,同时又有新鲜感。它们不仅仅属于女性,也属于男性。换句话说,我强调女性视角重要的同时,也希望强调女性所写题材的普遍性,强调人类书写主题的共通。
现在经常有人会对我说男人也可以写“爱、秘密和远方”,我说对呀,这就是我希望大家意识到的,去掉对女性的刻板印象。我很高兴大家正在接受这些,能把女性从那些陈旧的话语里解放出来。说到底,承认并尊重作为女性的感受,不掩藏,把基于女性视角所看到的写下,是对平等的确认,也是对写作自由的追求。
女性视角的存在,有助于让我们成为一个有独立思考力的人
北青报:在做书榜和年选的过程中,您收到过哪些印象深刻的反馈?
张莉:不少作家都跟我反馈,同学们的评语写得好,很诚挚。看到这些出生于1998年、1999年、2000年的青年写作者、青年研究者的评论,作家们会有一种知音之感。不过,我也会激励同学说这个作品的确好,但它的缺陷或者令人遗憾的地方是什么呢?不是故意挑刺,而是说每部作品有优点就有缺点。慢慢大家也会有这方面的意识,不仅仅要看到作品的优点,也要看到作品的不足。
我希望能够用我们的工作,让更多女作家的文学成绩被发现;希望“持微火者·女性文学好书榜”能够成为中国女性文学的领读风向标。
北青报:在您看来,女性视角的存在,对于女性写作有哪些影响或意义?
张莉:不能要求我们的电影和小说都是女性立场、女性精神的写作,但是作为女性可以有自己的女性视角的阅读。女性视角的存在,有助于让我们成为一个有独立思考力的人。不是说所有女性都天然具有女性视角,它是后天习得的。我愿意站在一个更低微的女性的立场去看世界。比如当一些社会热点事件发生的时候,大部分人,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天然会站在那位女性的角度,会站在相对弱的一方,这就是女性视角。
四年前很多作家不愿意说自己是女性作家或者女性写作,但今天已不再羞于谈这些
北青报:您的《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是站在历史的角度和眼光去看100年来的女性写作,在这样的研究中您关注到哪些现象?
张莉:我喜欢从100年前的历史深处看女性问题,这会让我更深切地理解每个人的处境、我们的时代处境。时代在慢慢向前,大家的性别观意识和女性意识都在醒觉。四年前我做性别观调查的时候,很多作家不愿意说自己是女性作家或者女性写作,但今天大部分女作家会直言自己是女性写作。我们不再羞于谈这些词,这便是一个很大的可喜的进步。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我们能明显感受到,社会的土壤发生了变化,作家们都感受到了这个变化。
北青报:在今天的年轻人身上,您是否看到新鲜的变化?
张莉:我和两位年轻同事共同开设的“女性文学研究”这门课,教学计划是不超过100人,上课的时候我看到过道里都坐着同学,从这些细微处,我能够感觉出年轻人的热情和他们对女性问题的关注。
第一次上课,我会请同学谈一下为什么来选这门课以及他们之前的阅读。他们的阅读趣味非常庞杂,而且也很有品位,这让我感到惊喜。班里也有很多男生选修,他们不是在猎奇,而且他们对很多问题的思考很深入。有个男生发言说他以前谈恋爱时会对女性有些刻板想象,比如说,好女孩儿必须乖、必须可爱。后来他突然意识到不能把自己的想象套到别人身上,要摆脱成见,这令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觉得新一代年轻人越来越有思考力。
女性视角让我面对这个世界变得更包容,也更懂得、更理解
北青报:女性视角为您的相关研究,包括您自身带来了哪些思考?
张莉:为什么要做女性文学研究呢?其实是让看不见的看见,让听不见的听见。有一次我跟朋友说,虽然大家看我的工作很多,既做女性文学好书榜、女性文学年选,也做女性文学研究,但实际上我做的只是一件事。这件事就是跟女性文学有关、跟当代文学发展有关。
女性视角并非与生俱来,它是一种价值观,也是可以学习的方法论。我是女性视角的受益者,它让我面对这个世界变得更包容,也更懂得、更理解。以前我写博士论文时看的都是著名作家,慢慢地我喜欢看到普通女性的命运,我愿意和她们共情;现在我更愿意站在低微处,看到那些所谓的不成功、不如意的普通人的生命光泽与力量。我希望自己在阅读时,能打破暗处发现新故事,让我们成为不驯服的读者。
做女性文学研究,我认识到世界的辽阔,看见了无数的她。也认识到个人的有限性,我对自己的理解不一样了,我喜欢做事,心无旁骛地做事。我深切认识到,在个人生活的行程中,能够一以贯之地做一件事,努力把一件事做好,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更多
更多

罗振亚:关于当下诗歌现状与未来的对话
“中华传统文化对新世纪诗歌构成的是精神思想和艺术技巧的综合性辐射,对当下诗歌具有正面价值的引发和渗透。我们真应该静下心来,细致考辨其间的运作规律。”
 更多
更多

柴德赓与刘乃和:亦师亦友三十载
《柴德赓日记》中师友、同事人名出现最多的是陈垣,其次是刘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