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下琐言》:19世纪的南京记事
编者按:2024年4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大学问出版了历史学者李孝悌的《琐言赘语:明清以来的文化、城市与启蒙》一书,该著是他在社会文化史代表作,揭示明清以来文化、城市与思想的多个面向,展现隐藏在城市深处和历史尘埃里的生活真相。全书内容横跨五百多年的历史,从明代洪武年开始延续到“五四”白话文运动,涉及城市社会、思想启蒙与文化等多个议题,亦对近现代文学研究有“借镜”之功。经出版方授权,我们特遴其中第四章《白下琐言》(节选)发布,以飨读者。这一部分通过对《白下琐言》介绍与研究,巧妙地展示了考据与传说的交织,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理解地方史编纂的过程和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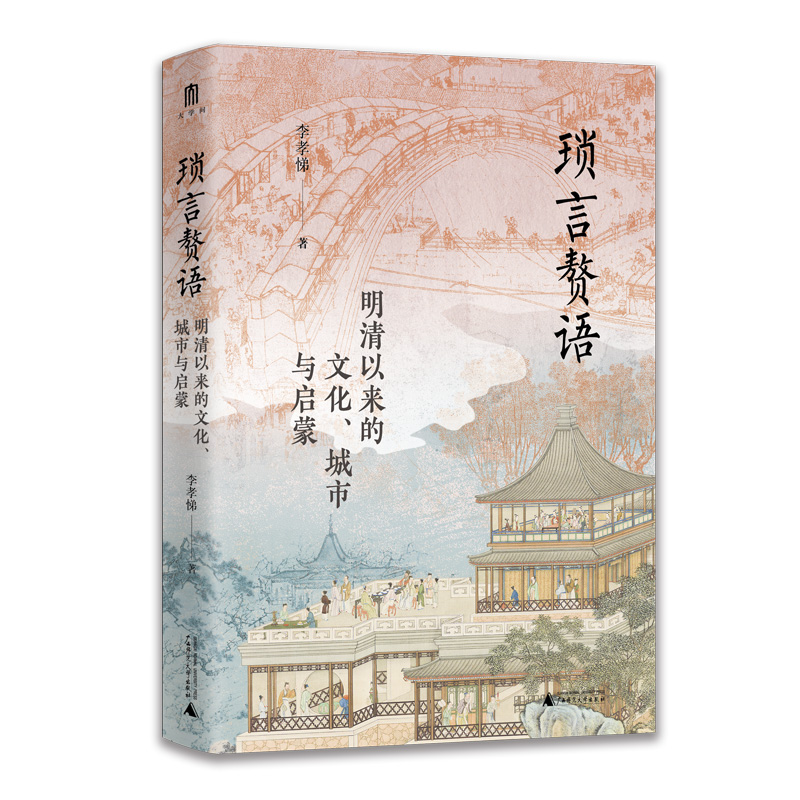
《琐言赘语:明清以来的文化、城市与启蒙》,李孝悌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4月出版
在明清士大夫撰写的南京杂忆中,甘熙的《白下琐言》无疑是继顾起元的《客座赘语》之后,另外一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在表面上,这些作品都是依笔记小说的体裁,一条一条,没有结构、没有主题地撮集而成,杂琐而不成体系。但是,透过地方志编纂者的摘录、标举,这些琐屑、非正式的个人记忆,被纳入官方、正式的历史记载中,成为地方历史的系谱和大叙事的组成因素。顾起元的《客座赘语》被康熙七年(1668)陈开虞主修的《江宁府志》大量采用,以其程度而言,固然是一个相当特殊的案例,但就笔记小说与方志记载的关系而言,并非仅此一家实现了突变发展。甘熙的《白下琐言》就是另外一个例子。
同治年间续纂的《江宁府志》,对金陵叙事的系谱和传承作了非常清楚的排序:
金陵古帝王州也。……其志名胜,则权舆于唐许嵩(《建康实录》)、李吉甫(《元和志》亦旁涉古迹),迨宋张敦颐(《六朝事迹类编》),……元张铉(《至大金陵新志》),明顾璘(《金陵名园记》)、陈沂(《金陵古今图考》)、顾起元(《建康宫阙都邑图》《客座赘语》)、盛时泰(《金陵纪胜》)、周晖(《金陵琐事三编》)、曹学佺(《名胜志》),诸人益侈且备。
这一连串包含方志与笔记的南京叙事系谱紧接着的,是陈开虞和吕燕昭分别于康熙七年修纂的《江宁府志》和嘉庆十六年(1811)编撰的《新修江宁府志》。很明显,在同治年间府志修撰者的眼中,顾起元和周晖等人关于南京的杂记作品,和《六朝事迹类编》《景定建康志》《至大金陵新志》及清朝的两本官修府志,已经不分类别地成为南京千年历史叙事的一环,而他们自己要做的,则是为这个一脉相承的历史叙事,做补强更新的工作:
陈、吕二志之所采掇也,事历八代,阅千数百年,遗文坠绪,变更而湮没者多矣!兹纂旧闻,继前轨有所不容己于记者。所以壮山川之灵秀也,作《名迹志》。
甘熙的《白下琐言》就是在这个与时推移、补强更新的原则下,进入了夹杂着官方叙事和私人杂忆的历史的殿堂:
高岑《四十景图》、余宾硕《金陵览古》,国朝书也,然于嘉道间尚远,惟王友亮《金陵杂咏》、陈文述《秣陵集》、周宝偀《金陵览胜考》、金鳌《待征录》、甘熙《白下琐言》、李鳌《金陵名胜诗钞》,皆以其时之人话当时。
从下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来,甘熙写《白下琐言》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将来的方志编纂者提供可信的数据;而在写作过程中,顾起元的《客座赘语》是重要的参照点和对话对象。在甘熙过世后不久,同治版府志的编纂者,就将他和顾起元及其他二十位作者,共同纳入建构南京历史论述的众神殿中,这无疑是最大的身后哀荣。甘熙的《白下琐言》虽然无法像《客座赘语》那样,在府县志的层级占据许多篇幅,但仍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治十三年(1874)刊刻的《上江两县志》,在列女、忠义、贞烈、名宦、乡贤诸卷外,于卷二十三单独列一卷《忠义孝悌录》,我怀疑是因为受到甘熙的启发。传统的官方史书中,虽然有孝义传,但并无以“忠义孝悌”命名者,袁枚刊修的《江宁新志》也只用了“孝悌传”之名。而甘熙在道光二十年(1840),有感于“忠义、孝悌散见群籍,未有裒集之者”,因而参考史传、志乘的记载,编成《金陵忠义孝悌祠传赞》一书并刊行。
我怀疑同治《上江两县志》使用“忠义孝悌”这个特殊的词语并以其为主线另立专卷的另一个原因,和这套方志的编者有关。在八个方志分修者中,江宁试用训导甘元焕是甘熙的堂弟,在甘家藏书楼毁于太平天国之乱后,一直试图重建。另一位江宁廪生陈作霖则显然对甘熙的著作了如指掌。由陈作霖自己编著的一系列金陵乡土志中,我们又可以看出甘熙的《白下琐言》已经超越了《客座赘语》,或者至少和《客座赘语》并列,成为晚清乡土记忆最主要的源头。
根据陈作霖自己的说法,他“隶籍建康,留心文献,两襄志局”,在修纂方志外,又编纂了《金陵通纪》《金陵通传》两套卷帙浩繁的大论述。而在此之外,他又进一步写了一套琐细的乡土小志。在这些关于河流、桥梁、里巷、街道、物产等细部的乡土记事中,陈作霖大量地援引了《白下琐言》的记载。1917年,陈作霖的儿子陈稻孙秉持父亲写作《金陵琐志》的精神,出版了《续金陵琐志二种》。有趣的是,不论是友人为《金陵琐志》写的序言,还是陈稻孙自己写的《凡例》,都赋予《白下琐言》更高的地位:
此则《板桥杂记》系兴替于简端,《白下琐言》陶哀乐于弦外者矣!
是志所采,专以府县志为主,导源于《建康实录》《景定建康志》《金陵琐事》《六朝事迹编类》《白下琐言》诸书,而辅以《板桥杂记》《客座赘语》及家君《金陵通纪》《通传》。
这两则引文显示,到19、20世纪之交,余怀《板桥杂记》和顾起元《客座赘语》问世两三百年后,对于晚明南京的描述和追忆,仍然在发挥影响。在19世纪中叶问世的《白下琐言》,由于时代切近,对当时人的乡土论述,显然有更大的形塑作用。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的动乱,固然将南京的历史发展带向一个迥然不同的方向,并给南京的城市景观和许多人的生命历程带来巨大的冲击。但从陈稻孙写于1917年的凡例中,我们看到一个源于唐代《建康实录》的历史记忆,如何跨越朝代的断裂,绵延千年而不断,并将官方的帝国都城叙事和方志的传统,透过赘语、琐言及乡土志一类更细部、更地方的私密性叙事类型,向下穿透,构成一个坚实、绵密的记忆之网。
…………
除了是一位忠孝两全的儒者,甘熙另一个留给亲朋故旧和当代南京文献编纂者的主要印象,是藏书家和方志学家。尹晓华在2007年为《白下琐言》写的导读的第一句话就是:“《白下琐言》为清代著名学者、方志学家甘熙所著。”这为甘熙的生平志业和《白下琐言》的命意所在,作了最基本的定位。而这样一个热衷于乡邦文献的方志学家的形象,不论是在《白下琐言》的记载,还是在序言、跋文中,都清楚地显现出来。根据参与《同治上江两县志》编纂工作的甘熙族弟甘元焕的说法,甘熙早年家居甘氏大院期间,就热衷于地方掌故,在和地方士绅名人的交游宴集中,掌握了各种关于地方的细节知识,积累而成《白下琐言》一书:“先仲兄闳博耆古,专意经世之学。……早岁里居,耽志掌固。生长都会,游止鳞掌,长德巨公,风流弥劭。承平之宴,饫闻绪论。嗜记日多,笔札尘积。《白下琐言》,此其一也。”
而根据甘熙的姻亲、在金陵为诸生十年的方俊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所写的序,可知甘熙从嘉庆中期以来,就利用津逮楼丰富的藏书,开始撰写《白下琐言》一书。方俊写序时,太平天国运动还没有发生,甘熙和相知的友人已经在期待新的方志编纂者采用《白下琐言》的记载:“异日贤守令重修志乘,从之考献,必将有取于是书。”1853年,太平军占领南京,摧毁了南京的重要城市坐标大报恩寺,地方文献也被大量摧毁,津逮楼的大量藏书付之灰烬。城市的残破和典籍的丧失,让同治年间县志的编纂者,感到空前的压力:“惟金陵之被兵也久,残破甚于他郡。昔之炳乎焕乎其文物者,已凘为冷风,深惧菲材不足振兴治术。”“向闻金陵多藏书家,兵燹后典册灰烬,台阁簿籍掌故无考。即有好古搜讨之士,安能凿空而冥索乎?”负责分修工作的甘元焕,在《白下琐言》的跋序中,也说到同样的窘境:“同治、光绪之交,踵开郡邑志局,搜求遗籍,百不获一。嘉道前事,茫如堕雾,何况寝远传闻异辞。”《白下琐言》对方志编纂者的重要性,在这种困局下,益发突显出来。另一位跋文作者,就直接指出甘熙在战火前从容撰写的《白下琐言》,在战火之后更值得感激:“若夫彝鼎图书之嗜,贤者或訾为玩物丧志,而不知古人精神所寄,往往质疑订坠,有不可思议之功用。居今日而言古学,殆有不能已者。金陵自粤匪之乱,朱氏之书已沦劫火,津逮亦仅有存者。先生独能于丧乱之先,从容纂述,俾后人受而守之,由今以思,抑岂非盛幸耶?”
甘熙对金陵掌故、文献的兴趣,除了源自和顾起元一样的博学多闻和乡土之情,和津逮楼的丰富藏书显然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甘熙和顾起元一样,充满了对南京历史传承的感情,除了借着自己“往来无白丁”的家世渊源,从和地方耆旧、文人的交往、宴饮中,记取各种地方传闻、叙事,更善加利用津逮楼和朱绪曾等人的藏书,让自己的琐屑之谈,处处显露出乾嘉考据之学的影子。前面曾提到顾起元在搜求地方文献时,对“金陵古称都辇,乃自国朝以上,纪载何寥寥”所发的感慨。但不论是“讹阙过半”的《金陵新志》,还是“不知存亡”的《景定建康志》,都被安稳地放置在津逮楼的一角:“前贤著述有关乎是邦考证者,近多失传。家大人留心掌故,凡此类之书,搜访尤殷。”这些近多失传,而被甘福刻意搜访得来的南京地方文献,从唐代许嵩的《建康实录》、宋张敦颐的《六朝事迹类编》,到朱之蕃的《金陵图咏》、顾起元的《客座赘语》、周晖的《金陵琐事》,近四十种,其中当然也包括了顾起元特别提到的《金陵新志》和《景定建康志》。
除了自己家中收藏的丰富文献,甘熙写作过程中也借用了同乡名人朱绪曾开有益书斋中的珍藏秘笈,互相考订,并和朱绪曾及另一位有相同志趣的地方文人金鳌一起讨论,“证析异同”。从同治版的《江宁府志》将金、朱、甘三人的传记前后并列这一个安排,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个士大夫的地方网络在传述地方历史上所占有的突出位置。这一小群对传述地方历史抱有殷切期待的文人士大夫,通过各自的家藏图书、文献搜集考订和相互讨论交流,为即将来临的府县志重修工作,奠定下扎实的基础。从这个脉络来看,不论是“待征”“诗汇”还是“赘语”“琐言”,都有了更严肃的时代意义。
就是这种为重修地方正史做准备的使命,让《白下琐言》这本原本应被划入笔记小说之类的作品,充满了乾嘉考据成果一般的气味。甘熙像考释经典一样,对地方文物、里巷、人物、地理位置,作了看似琐屑的考证修订。随手可得的津逮楼藏书,也让他的考证工作,更多了一份学问家的气息。
大山寺在牛首山西,见《江宁县志》。……凡牛首以西诸水,悉由此出,形家所谓水口罗星也。其上有古寺,俗呼曰“太冈寺”,有香楠树一株,大数围。……《县志》又载:“团林庵在凤台门外小丹阳地,元顺帝三年建。”今其庵尚存,然小丹阳距聚宝门九十余里,安可以“凤台门外”四字概之耶?故修志非土著人而留心掌故者,断不可以从事。
这条记载有几个可以注意的地方:一、方志对地方建置古迹记载得很详细,一庙、一庵都尽可能地标列;二、这些地方建置古迹值得记载,是因为其历史常常可以上溯数百年;三、甘熙对山川地脉、堪舆之学的兴趣,在这条记载中已可一窥端倪;四、甘家故居刚好位于城南聚宝门外的小丹阳。外地来的士绅官员笔下大致如此的记叙,在一个留心考据的在地者眼中,是不能容忍的粗疏,所以甘熙在下笔时,往往用相当强烈的字眼,指责这些外地来的方志编纂者。下面几个例子,都显示了甘熙对这些外来方志编纂者率尔操觚的不满:
又,《府志》及《上元县志》所载乡贤,有大学士蒋廷锡。蒋公常熟人,雍正六年授文华殿大学士,卒谥文肃。不知修志时何以错误至此。
杏花村,在城西南凤游寺之右。《府志》谓:“信府河,凤凰台一带即是。”殊无分晓。信府河乃今长乐渡,有汤信国公祠,一东一西相去悬绝,何与凤台牵?混言之耶!然则修志者,必细心参考,不可率尔操觚也。
凤游寺因凤凰台而建,位于城西南,是晋时瓦官寺的所在,因为诗人李白的名句“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而广为后世人所知,是南京著名的古迹和旅游地。方志作者不分东西,混杂而谈,难怪引起甘熙的怒火。
秦钜、秦浚墓在处真乡移忠寺侧,见《建康志》。按今木牛亭为处真乡,桧墓在其地,予已详考之。钜字子野,桧之曾孙也。嘉定间,通判蕲州。金人犯境,与郡守李城之协力捍御,城破巷战,死伤略尽。归署自焚死,二子浚、瀈从焉,后封义烈侯,见《宋史·本传》。盖死于蕲州,归葬于此也。浚为钜子,而袁枚所修《县志》误以为弟,则谬甚。
秦桧作为奸臣的代表,同样引起地方学者的侧目,顾起元和甘熙都曾对其墓地所在,有所考证。秦钜虽然是秦桧的后人,但父子三人为国殉节,满门忠烈,在重视忠义孝悌的甘熙眼中,其生平事迹自然不能随笔带过,县志的错误因此显得特别刺眼。
基于同样的忠奸之辨,甘熙用了相当的篇幅,对南京贡院土神纪纲的身家来历,作了详细的考辨:
贡院创于明永乐间,乃籍没锦衣卫同知纪纲宅。……明德堂有《应天府尹王弼碑》可据。纪纲事详《明史·佞臣传》及王凤洲《锦衣卫志》、陆粲《庚巳编》。而新修《府志》以纲为元集庆路行省丞相,与御史大夫茀寿偕死,葬于明远楼下,灵爽赫濯,为贡院土神。非特时代讹舛,抑且忠佞倒置,盖沿《金陵闻见录》之误,而不考碑纪使然也。朱述之绪曾作七古辨之云:……弇州山人撰《四部丛书》,特笔罗其详:“……府尹王弼撰碑记,始末备载何煌煌。迩来志乘不稽古,讹为丞相殉戎行。御史行台最忠烈,肯与此辈相颉颃。《元史》无征《明史》著,况复碑文俨在堂。忠佞倒置非细事,乌可清浊淆沧浪。”
语气一转,甘熙又进一步指出,方志的错误,如何影响到后来写作乡土纪闻之类小叙事的作者:“钱塘陈退庵先生文述,刻有《秣陵集》八卷,皆题咏古迹,诗词瑰丽。然其中事实讹误,考证颇疏,如谓吴鲁肃墓在上新河,乃沿王葑亭《金陵图咏》之误;以覆舟山为太平门外,……杏花村在城南信府河,乃沿吕太守新修《府志》之误。……可见古迹一门,土著人非经考订,犹失其真,况异乡人乎?甚矣!修志乘者之宜慎选也!”
甘熙在此处,以博雅的乾嘉考据学的精神,一一指出方志记载失误的根由所在。事实上,这些倒置忠奸的根本性错误,只要稍微留心史书或文献记载,就不该发生。晚明知名的文人学者王世贞已经将来龙去脉交代得非常清楚,但吕燕昭监修的嘉庆《新修江宁府志》仍然以讹传讹,而必须靠朱绪曾和甘熙这样关心和熟悉地方文献、掌故的人再一次郑重地提醒。甘熙对方志在这些事关忠奸的大节上所犯的错误,指摘严厉,在口气上和梁启超在《桃花扇注》中,对在重大史实、人物及忠奸问题上的错误的批评,如出一辙。这些批评,无疑让我们对方志作为一种地方官方历史的性质及其知识建构的方式、来源,有了一个重新省思的比较、参考点。《桃花扇》是文学、戏剧创作,大概很少人会用正史记载的标准来衡量其历史叙事的正确性,但梁启超因为担心剧作在形塑历史知识、历史记忆上的影响力远超过“正确”的历史记载,而对《桃花扇》的叙事严肃以对。
反过来看,因为方志披上了历史的外衣,被视为地方历史叙事中最正式,也最具权威的知识体系,我们往往忽略了方志编纂者在搜集资料、编纂史实的过程中的任意性及不可靠性。甘熙一再反复陈述的外行人和异乡人修志的结构性和制度性缺失,正是前述问题的一个主要来源。道听途说的传闻经过辗转誊抄,虽然被纳入方志的知识体系中,仿佛具备了史实的框架,但这种叙事与剧作家的想象及笔记小说家琐细、非正式的叙事之间的差异,确实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具体而言,如果我们将南京府县志中大量征引顾起元、周晖及甘熙的笔记小说中的记载这个事实考虑在内,势必会对形塑历史记忆和地方知识的过程,有更深入的体认。有趣的是,甘熙虽然用着乾嘉考据学者的口吻,批评方志编纂者笔下的谬误不实,念兹在兹地以为重修方志做准备的心情,撰写《白下琐言》,并果真如愿达成这个使命。但在同时,甘熙也用一种言之凿凿、真实有据的口吻,传述各种《聊斋志异》式的鬼魅故事,甘熙的南京记事因此像他既期许又批评的方志一样,在一个看似坚实的城市历史之中,编织了各种奇幻虚渺的传奇。里巷、院落、衙署和宅邸的暗处,既深埋着悠远的典籍文学,也随时有不可测度的幽灵倏忽而至,它们一一被网罗进甘熙的城南旧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