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进行一种事关存在的介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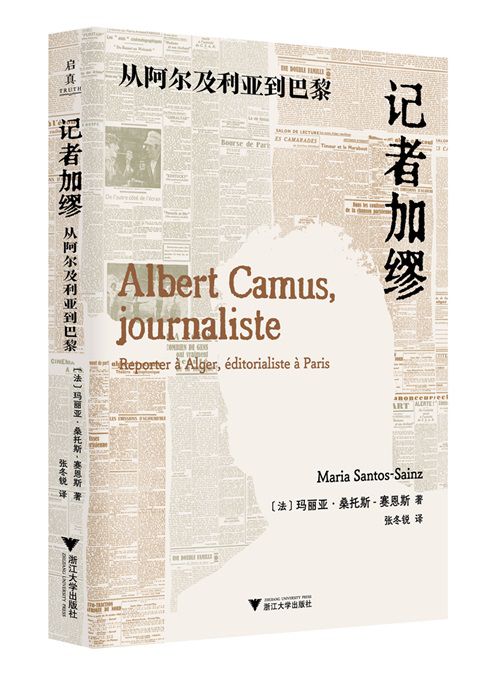
《记者加缪:从阿尔及利亚到巴黎》,[法]玛丽亚·桑托斯-赛恩斯(Maria Santos-Sainz)著,张冬锐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4年9月
那是1957年12月10日,在斯德哥尔摩举办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的日子。这些最负盛名的人中获得了当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加缪,依照传统,在官方晚宴结束之前发表了获奖感言。他强调了一点:“或许,每一代人都自信肩负着重塑世界的使命,但我们这代人知道,我们对此无能为力。然而,我们的使命或许更艰巨,即不让这个世界分崩离析。”
在那个时代的背景下,即冷战、反殖民斗争、帝国主义、独立运动、蔓延直至欧洲大陆的独裁统治及反叛的青年,所有这些因素同时并存。简言之,就是在解放和抵抗的背景下,这番言辞或许听起来谨小慎微,像是在后退或有所保留。然而,在60年后的今天看来,它比任何时候都更符合实际;而且,它远不是一种对谨慎或冷漠的邀约,而是对“介入”的呼唤。
这种“介入”不是企图使现实屈从于其信条的、具有狭隘派系观念的人的介入,这类人的介入并不明智,因为他们相信仅从政治角度思考是正确的,此外,其中一些人还认为自己说的是真理。加缪邀请我们去进行的是一种更不可缺少的介入:一种事关存在的介入,对我们可以作为自由的男人和女人的条件的介入。我们的自由需要我们,要求我们负起责任。我们要对世界负责,尤其对其意义负责;我们要对世界之内涵负责,也就是对其团结负责;我们要对世界之理性负责,反对会毁坏它的非理性。
赴自由之约,并不是给世界的失序增加出于恐惧的慌乱和出于仇恨的激动,这就像盖上一层使我们愈加不安的厚重而愚昧的面纱。相反,赴自由之约是寻求理解、苛求知晓、直面真实,尽管它令人痛苦和烦忧。为了能真正地自由选择、自主决定,我们需要看清一切,否则,我们只会成为我们幻想的玩物,被幻想催生出的灾难打败。
因此,《记者加缪:从阿尔及利亚到巴黎》一书并不仅仅是一部严谨精确、资料翔实的专著。通过展示这位作家当记者时的活动在多大程度上是实践这种介入——以寻求真相为首要目标的介入——的主要阵地,玛丽亚· 桑托斯-赛恩斯呼吁人们振奋起来。她的作品实际上是在敦促新闻业重新振作,并不断提升,找回自己的高度和深度,拒绝粗制滥造,同时与为之布下陷阱、使之丧失威信的败坏行为做斗争。
1944年夏天,巴黎解放时,加缪在最初发表于《战斗报》(Combat)的社论中做出了承诺。而从《阿尔及尔共和报》(Alger républicain)最初的调查,到《快报》(L’Express)最后的专栏文章,加缪发表的这些作品从各个侧面让我们看到了他对这些承诺的忠诚(提到巴黎的解放,我往往会想起勒克莱尔师的西班牙共和军战士也是其中的英雄)。加缪于1944年8月31日这样写道:“我们的欲望越是习惯沉默不语,就越是强烈,它将报刊从金钱中解放出来,赋予其风度和真实性,这种风度和真实性将公众带往其能到达的最高处。于是,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价值往往由其媒体的价值体现。如果报刊确实是一个国家的发声筒,那么我们决心站在自身的角度,作为一支微弱的力量,通过优化国家的语言,来提升国家本身。”
这个项目一点都不过时,玛丽亚·桑托斯-赛恩斯的最大贡献是重新赋予了它一切现实性——如果不是紧迫性的话。在媒体经受风浪的日子里,在这个行业受到威胁、在记者这个职业失去稳定性的时刻,她的这本书对于记者(以及公民,这两者并肩而行)而言是一部抗争指南。她邀请我们向加缪学习,在索求公众知情权中,带着对公民的责任,重拾勇气,找回尊严。当娱乐腐蚀了资讯,当集中摧毁了多元,当扼杀了真相,新闻业就只能进入抵抗状态,除非它改变自己的看法。这一切只是出于职业责任。没有自命不凡,没有妄图虚名,只是出于生存的需要。
在阅读玛丽亚· 桑托斯-赛恩斯的文字时,我不断想到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真理与政治》(Vérité et politique)中的警告。这篇文章写于1967年,我认为它是我们这一职业真正的哲理性宣言。她坦言,如果没有记者,“我们将永远无法在一个一直变化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方向,并且,从最直白的层面上讲,我们将永远不会知道自己在哪里”。这里我们又看到了加缪在1957年提及的这个萎靡不振的世界——失去方向,步入歧途,被夺走了路标。
但是,阿伦特补充说,只有当上述记者是不断寻求“政治意义上最重要的真相”的审慎仆人,而不是爱好发表意见的机会主义狂热者时,这种民主理想才有价值。这位哲学家声明:“如果关于事实的信息不能确保是真实的,如果辩论的对象不是事实本身,那么意见自由就是一场闹剧。”然后她提出了这样的看法:“当代历史上有很多例子说明,说出事实真相的人被认为比真正的反对者更危险、更具有敌意。”这一点在今天得到了充分的证实:在我们这个充满即时新闻的通信时代,没有国界、没有延迟,许多揭秘者只能落得悲惨的命运,如朱利安· 阿桑奇(Julian Assange)、切尔西·曼宁(Chelsea Manning)、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这里仅提及世界上最有名的揭秘者,他们是捍卫普遍知情权的英雄,对抗着国家或金融权力机构的不正当秘密。
阿伦特和加缪这一代人被他们亲历的犯罪、战争、屠杀等悲剧残酷地夺去了天真。两人都以大卫·鲁塞(David Rousset)于1946年从集中营世界返回时表达的那种清醒进行思考:“正常人不知道一切皆有可能。”“一切皆有可能”的“一切”包含了人类最糟糕的一面,即对自身人性的否定。唉,当我们眼见“恐怖主义与武力镇压的那场血腥婚礼”自2001年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庆祝时,我们又一次领会了这个道理。
这些话看起来像是今天说的,事实上来自以前。这些话出自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对恐怖主义毫不客气的加缪;它是一种抗争的方式,这种方式不再“是受控于某种政治的工具,不再寻求成为某种仇恨下的疯狂武器”。但是,正如他在广岛那颗原子弹造成的毁灭中当即看到的,那一刻“机械文明达到了其野蛮程度的顶点”,他也察觉到了这是一场没有回旋余地的剧变——轻描淡写的酷刑、秘密监狱、特殊状态、被践踏的基本自由——其中“每个人都以他人的罪行为借口,以便更进一步”。
但我们怎么能忘记,今天,这种指望靠恐怖主义带来的恐慌来抛弃人民、削弱民主的恐怖政治,诞生于之后会是媒体谎言的国家谎言,再以各种新保守主义的面目传播到美国之外?我们怎么能忘记,即便是所谓高质量的北美媒体,也相信“基地”组织与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之间有联系的传言,相信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无稽之谈,相信布什政府的意识形态议程,而这些议程与具体的现实没有任何联系,无论联系有多小。简言之,我们怎么能忘记,对事实真相的压制允许了一场非法的、造成大量死亡的冒险?
加缪总是冒着让各个阵营的人不高兴的风险,拒绝那些具有安慰性的半真半假的说法,这些说法只寻求符合主流偏见,却罔顾现实。就像目的不能证明手段的正当性一样,任何正当的动机都不能宽容谎言的不正当性,对真相闭口不谈也是一种谎言。当下,这种孤立的独立态度引发了误解和疏远,造成了断裂和憎恶。加缪,一个无法被归类的极端自由主义者,他的生活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从长远来看,这种态度保有永恒的警觉,将使后代受益。
这部玛丽亚·桑托斯-赛恩斯追忆并重访“记者加缪”的作品就证明了这一点,啊,它是多么必不可少。因为,在我们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事变的不可能性与灾难的可能性并肩而行,新闻业极有可能再次被置于考验之中,受到灌输,被利益的重压阻碍,掉入金钱和权力交错进攻的陷阱。然而,解药就在这本珍贵的书,这份邀请我们沿着阿尔贝·加缪的足迹走下去的“新闻批评”之中。
它要求——它已经告知我们——“记者本身对新闻工作的深刻质疑”,即记者对其工作的意义、职业的责任进行的反思。加缪在1944年9月1日《战斗报》的一篇社论中写道:“什么是记者?他首先应是一个被认为有思想的人。”这个答案谨慎又讽刺,它想表达的是:记者应是一个质疑自己工作的意义的人,一个不断忧虑、自问、怀疑的人,若他知道自己使命的重要性,便更应如此。在这个意义上,加缪认为,新闻界应站在犬儒主义和麻木不仁的、唯利是图和投机取巧的、因循守旧和机会主义的新闻业的对立面,索求真相这个职业要求也是对人生理想的忠诚。从他1946年3月28日于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举办的演讲会中,可以看到这一观点的雏形,第一所新闻学院也是在那里创建的。“如果什么都不相信,如果一切都没有意义,如果我们不能确认任何价值,那么一切都可以得到允许,什么都不重要,”他解释说,“那么就没有善与恶,希特勒既不对也不错。”若是如此,“正确者即成功者,在他成功之时,他就是正确的”。
这种胜利者的光荣哲学总是满足于对战败者的羞辱,阿尔贝·加缪用劳动者的谦逊德行与之对抗。在这个演讲会上,他谦逊地说要“坚守岗位,做好本职工作”,使一个“警察、士兵和金钱的世界,变成一个男人和女人的世界,充满有成果的工作和恰到好处的闲暇的世界”。
很明显,我们这里谈论的介入是一种建立在根本民主之上的境况,其目的是达到某种高度的民主,在这种民主下可实现日常人道主义、自由商议和广泛共享、社会公正和个人自由、真正的人民至上,而非暗中进行的寡头私有化。在这条充满希望和抗争的道路上,从弱者到强者,知情权是通过知晓来实现解放的和平武器。作为深耕“当下”的工作者,记者是为这一基本权利服务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参与到这场战役中。当然,他们必须达到负起这一责任所要求的高度。
玛丽亚· 桑托斯-赛恩斯这本书将新闻与批评——公民对媒体的合理批评和专业人士必要的批评意识——相结合,是一个愉快的邀约,面对这一需要,我们在所不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