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子超:旅行写作的核心是遇见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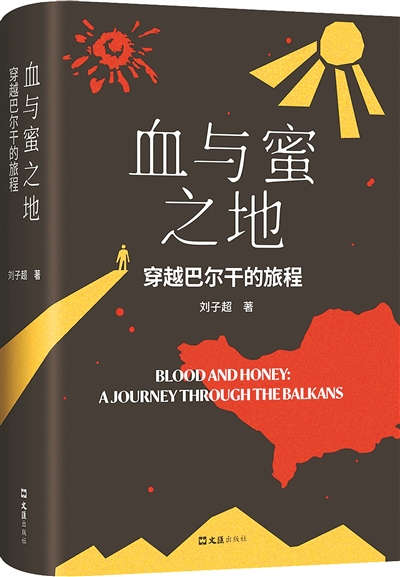

继《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 后,作家刘子超再次跃入东西文明的交汇地带——巴尔干,为读者带来最新著作《血与蜜之地——穿越巴尔干的旅程》。
从北到南,由冬入春,刘子超穿越素有“欧洲火药桶”之称的巴尔干半岛。8个国家,23个城镇,再度见证世界的细碎与广阔。
在斯洛文尼亚,他闯入一场诗歌沙龙,看见诗人如何用语言重建家园。在克罗地亚的边城,瞥见昔日帝国的余晖,在一个老侍者身上找到过去的优雅。在黑山的深夜,少女接线员忙着为遥远的美国人订比萨,自己却从未尝过一口;活在南斯拉夫旧梦中的克罗地亚青年,可以修好一切东西,却修不好自己;结识塞尔维亚的电商教父,他感受着全球化的浪潮。
在刘子超笔下,巴尔干变得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更像一个形容词,充满伤痛、挣扎、求索和希冀的复杂含义。穿越历史漫长的阴影,抵达布满弹孔的时间现场,一路收集当地人的故事,去探索一个更具普遍性的问题,一个始于巴尔干却与我们每个人都相关的问题: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下,我们何处为家?
文学评论家李敬泽指出,这本书写的是巴尔干,但是我们从中能够理解现代社会以来全球存在的各种各样的矛盾和暴力,所有这一切在巴尔干表现得非常集中典型,通过巴尔干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世界。
“中国现在的经济利益和人员往来深深地嵌入了世界各地,但我们对世界的很多地方其实并不了解,它们的文化历史乃至于亲身的了解,无数中国人走到了世界各地,但是真的把自己写下来,我如何用身体用自己的心去领会这样一个陌生的世界其实是很少的。”
《血与蜜之地——穿越巴尔干的旅程》是刘子超的第四部旅行文学作品。《午夜在降临前抵达》书写的是欧洲大陆,《沿着季风的方向 : 从印度到东南亚的旅程》集中在亚洲地区,刘子超说计划在未来继续书写世界各个地区,就像拼图一样完成自己的旅行写作。李敬泽赞叹这是一个宏伟的构想,“一个中国写作者,如何经历陌生的世界,如何书写陌生的世界,特别有意义。”
他还敏锐地意识到一种新的文体的诞生,“以前各种各样的游记,包括出国,谈谈历史、谈谈文化、谈谈景色就完了,什么叫旅行文学,旅行文学不光是要去认识那个陌生的世界,那个陌生的世界最重要的是由陌生的人构成的,去认识那些陌生的人,所以整本书我特别喜欢他和巴尔干各种各样陌生的人的交集,特别有意思。”
刘子超说,在走过一些弯路后,他渐渐得出了那个朴素的观点:旅行写作的核心,不仅仅是从外部旁观,更需要深入接触和理解那里的人。书写人类的命运如何在漫长的时间、记忆和地理的褶皱中发挥作用,正是旅行写作所要追寻的目标。
呈现面对未知世界时探索的过程
北青艺评:我记得你曾说你的上一本书《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是一个偶然性的产物,这本书呢?
刘子超:我写中亚那本书的时候,最开始就是想自己去那边走走,因为那时正好有一些签证的便利措施,就利用这个机会去了。我准备写的其实是俄罗斯,我当时坐火车横穿西伯利亚,从海参崴一直到莫斯科,每站都会下车,去那些主要的城市。然后,我还从伏尔加河的源头一直走到了入海口,我觉得这是俄罗斯的两个动脉一横一纵,可以把这个国家的东西串联起来。但是回程的路上,正好发现有一些中亚的签证便利措施就去了,去了以后,突然就觉得这个地方可能更有魅力。我一旦产生兴趣就会不断去往这个地区。
巴尔干这本书说来也是偶然。我出发的时候国际旅行还没有完全恢复常态,我当时先飞往巴黎,但是行李还没有托运到,本来我想去非洲,结果行李还在北京,因为又是冬天,欧洲很冷,我就往南走,往相对温暖的地方走,于是去了西班牙。因为当时国际航班很少,下一班从国内来欧洲的航班(上面有我的行李)目的地是荷兰,我又临时改了计划往北走,去取我的行李箱。路上就会经过比利时,那里有很多修道院的啤酒厂,我也挺喜欢喝啤酒,喝完啤酒出来经过大片墓地,都是一战时期士兵的墓碑,于是联想到一战导火索发生在萨拉热窝,那时我第一次想到巴尔干。
北青艺评:确定要写巴尔干你怎么规划行程呢?
刘子超:斐迪南大公的遗体先是从巴尔干腹地运抵的里雅斯特港,再由铁路运回维也纳。这让我想到,或许可以循着这一路线,从的里雅斯特出发,开始我的巴尔干之行。正好,的里雅斯特也是我的第一本书《午夜降临前抵达》的终点。
北青艺评:所以这么多偶然性,你在去一个地区旅行之前并没有做太多学术或研究上的准备?
刘子超:因为我这些年都在全世界旅行,对一个地区有一定的认知,但是具体他们之间是怎么回事,我也是一边走一边去学习,我希望我呈现的是一个人在面对一个未知世界,怎么去探索的过程。普通的读者,对世界上大部分地区都不会有那么深的了解,但是它不能阻止我们去开始这么一个过程。如果你去写一本学术的书,而不是一本文学的书,需要你做大量的准备,看无数的文献,但你一生的精力可能也就只能局限在一个地儿了,而不是说每本书都要处理不一样的地方。 对于我来说,阅读是一种学习,行走也是一种学习,学完了也可以再走走,完了可以再学,这么一个过程。我觉得那种切身的体验在最开始是更重要的,因为只有当你有了切身体验,你才能对它真正感兴趣,然后你才知道接下来要读什么。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先去体验,你就会慢慢的有一些感受。
另外,知识也是一张网,你今天在这个国家,明天在别的地方,你觉得了解的东西是分散的和零散的,但我后来发现不是,很多东西都能慢慢串联起来,所以当你旅行越来越多,你的阅读越来越多,这些东西都能慢慢串起来,以前读的那些书也可以帮助你理解新的地方。
既可以置身其中 又可以超脱其外
北青艺评:你在这本书里写了很多当地人,和我们记者采访要提前联系做准备很不一样,大部分好像也是你偶然遇见的?
刘子超:我觉得旅行写作很有意思的就是,有些事你不是之前就能都想清楚的,虽然我决定了把的里雅斯特作为第一站,但是具体要去做什么写什么我是不知道的。我在书里写第一章序幕的时候,写到我去了边境线上的一个葡萄园,然后边境线正好穿过葡萄园,把这个葡萄园一分为二,在南斯拉夫时代一半归了南斯拉夫,一半归属意大利,那也是我在看地图的时候,偶然发现了有这么一个葡萄园,正好跨越两个国家的边界,感觉那里可能有故事,也不知道是什么故事,会遇到什么人,但是就去了。果然到那里 ,我就碰到了葡萄酒庄园的庄主,然后他就开始讲当年家里的房子正好被边境线横穿过去,所以这房子一半属于意大利,一半属于南斯拉夫,他开玩笑说,当年他得有护照才能从自己家的一边到另一边,他的房子他的葡萄园被整个大历史切割了,到了欧盟时代以后,他才把原来属于南斯拉夫的那片收回来。这些故事都不是事先想好的或者设计好的,旅行写作对我来说好玩一点就是你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在寻找线索,然后循着这些蛛丝马迹去发现更多的东西。
北青艺评:就像一个城市的侦探。
刘子超:有点这个意思。旅行者还有一个很大的乐趣就是你作为旅行者的特权。你既可以置身其中,又可以超脱其外,没有其他的身份可以给你这样的特权,我会充分去利用或者说享受这个特权。另外,旅行的意义在于亲眼亲身去体验这个世界,而不是算法所塑造的世界。
旅行写作 记忆有它的筛选功能
北青艺评:你的写作习惯是怎样的?一边旅行一边写作吗?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事情你如果不立即把它记下来的话,很容易就会忘记。
刘子超:我在旅途中其实完全不正经写,但是我会每天会做一些笔记,会随身带着笔记本,我做的笔记可能是一些细节或者一些关键词,因为如果你认识了一个人,他跟你讲了他的故事,这个故事其实你不是特别容易忘记,而比较容易忘记的是一些细节,而那些细节使得写作是有质感的。故事,我会依靠记忆,记忆有它的筛选功能。我一般来说,这趟旅行持续了半年,我回去以后还会再放一段时间,有的东西沉下去,有的东西浮起来,这个过程我觉得也是很奇妙的一个过程,有点像威士忌酒厂,他们把酒液放到橡木桶里本来是满的,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你再打开橡木桶会发现酒液下沉了一点,酒厂的人称为“天使的分享”,过去的人们喜欢把这个酿酒的过程想象成小天使偷偷品尝威士忌,我觉得记忆也有这种功能,有些东西会蒸发掉,但是那种被蒸发掉以后,留下的东西反而更精粹,它代表了你对这个事或者人最强烈的感受和理解。
北青艺评:说到细节,你书中这样让人印象深刻的细节俯首皆拾,我还记得你写自己在一个火车站下了火车,然后列车长问你手上的东西是什么?你就说雨伞,然后结束了就走了。但是为什么你会加入这个可能是无关紧要的细节?
刘子超:对我来说写作最重要的是希望带着读者去遇见那些真实活在当地的人。如果你仅仅是传达历史知识,你对巴尔干有兴趣,你完全可以看历史书,它们会更专业,会写得更全面。但是在这些书里你是看不到这些活生生的人,特别是活在当下的这些人。我想通过他们的视野或他们的故事,或者说我跟他们之间的交集来作为这个地方的一个个小小的切片,然后把这些切片综合在一起的时候,你就能得出对这个地区的大致的图景。在这个过程中,你也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当地的历史和政治,但对我来说他们的重要性是低于那些人的,就像话剧,你需要给话剧搭一个布景,目的是突出在舞台上的人。
北青艺评: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这一点的?你在这本书的后记里说,在走过一些弯路后,渐渐得出了这个朴素的观点?
刘子超:大概在我的上一本书《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写到四分之三的时候。
北青艺评:特别是到了这一本书,真的感觉你的写作越来越接近“文学”,如果说第一本书《午夜降临前抵达》还比较“文青气质”,这本书就有一种越来越提纯的“文学性”。我不知道怎么描述这种“文学性”,除了那些“剩余物质”的充沛,也包括语言上的精进。有的句子完全是一首诗,我也是在看这本书里的第一章时才知道你也是个诗人。
刘子超:哈。当时在斯洛文尼亚为了能够迅速进入当地社会,我给他们作家协会写信,说我是来自中国的诗人,结果人家迅速给我回信邀请我去参加当地的一个诗歌朗诵活动。我的诗还没有英译本,我临时翻译了两首应付过去。我以前写过小说,也写过诗,现在诗基本就没写了,我觉得表达有很多不同的载体,旅行文学这种文体也很自由,小说的技巧能用在这类书里,比如塑造人物,对话氛围,风景描写。它也可以容纳对历史的看法,同时也可以是一首诗。
北青艺评:那你会想路上的这些素材也可以写成小说吗?
刘子超:我觉得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如果还是以旅行中遇到这些人为素材的话,写作上我的满足感是相同的。如果是写路上的故事,我会觉得旅行文学这个文体会比小说更自由,因为小说一定是你需要进入那个地方,你也需要给主人公一个身份,你不能说平白无故就写了一个塞尔维亚人为主角的小说,感觉很奇怪。毛姆也写了很多在路上遇到的故事,但是他的视角也是一个旅人的视角,如果是同样的视角,我觉得写小说和写旅行文学对我来说没有特别大的差别。
北青艺评:我还很好奇,因为你从第一本书到现在都会常常提到你在旅途中听音乐。
刘子超:对。我平时因为也喜欢听音乐,从高中的时候开始听,那时候主要听古典乐,工作以后慢慢地会听爵士乐,我觉得音乐能给旅程增加一个维度,你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选择什么音乐去听是跟周围的环境以及你当时的心情高度相关的,这种东西写出来以后,如果读者有兴趣,在读到那段的时候去找来音乐听,我觉得他更能感受到我当时感受到的一些东西。
北青艺评:旅行和写作这两者的关系对你来说是怎样的?你是因为喜欢旅行写作还是为了写作去旅行获取经验?
刘子超:我很喜欢旅行,喜欢旅行带来的那种自由感和探索感,它带来的快乐是别的东西很难去代替的。然后,我把这个过程又转化成文字,其实也是一个有趣的过程。我感觉自己的人生经验非常单一。我在北京出生长大,然后在北京一直上学,一直上到大学毕业,高中离家骑车10分钟,大学开车到家大概半小时。如果我集中在这些经历上只能写一两本书,但是你走出去以后,那些鲜活的素材俯拾皆是,而且又很少有中国作家去写这些地方。我觉得它能让你一直保持写作的可能性,一直有的写。
北青艺评:这确实很奇怪,如果你一直生活在一个地方反而没有去言说它的动力。有时候这种距离的远和近也是很有趣的矛盾点,我相信在北京也有同样有意思的故事,但是因为距离的切近,或因为身份的融入等等,让你没有办法有一个抽离的或者一种外部视角去写它。你没有打算写关于北京的书吗?
刘子超:可能会有。也许老了以后,老了以后就有距离了,你对童年也好,你对那些你经历过的事也好,就产生距离了,就可以去以一种更有“觉知”的方式去写它了,对,也许会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