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言午:风吹过扬兮镇
去年中旬,青年批评家岳雯从一堆快递里拿出一本书,本想随意翻翻,这一读就没有放下,那一整天,她一直沉浸在这本书里。“突然觉得天更亮了,疲惫也被洗涤干净了,有种强烈被治愈的感觉。”作为专业读者,这种感受并不多见。看到作者名字时,岳雯更吃惊,长期关注当代文学现场的她对这位作者却一无所知:“我不了解他曾写了什么,现在正在写什么,以及为什么写?”
2019年,许言午开始动笔写作《扬兮镇诗篇》。近二十万字,十个月完成初稿。在不疾不徐的创作节奏中,《扬兮镇诗篇》渐成一溪潺潺流水,自浙西群山间蜿蜒而出。先后经过两次修改,许言午将书稿发给早年间认识的一位出版界朋友季晟康,已投身儿童阅读的季晟康转交给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
“真的没有想到,像意外得到了一件宝藏。”从头至尾读完,韩敬群还想知道年轻人看法,便将小说交给社里两位90后编辑,获得一致称赞与肯定后,他决定,为这部长篇小说做试读本,这也是十月文艺出版社首次为一位不知名作者开展如此重要的出版环节。
几乎无人知道,二十年前,30岁出头的许言午曾写过两部长篇小说,一部发表于《收获》,另一部由民营书商出版,并未引起反响。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许言午同那个年代的学生一样,也有文学梦。他原打算,如果《扬兮镇诗篇》没有被出版社看中,就自费出版。“书架上有一本,也算给自己一个交代,这件事就过去了。”
写作这部小说的过程,相当平静愉悦,“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都是如此”。许言午认为,有价值的文学写作不仅表达对世界的看法和感受,也是对自我的再认识和塑造。《扬兮镇诗篇》于他,是一次愉快的复苏,一个新的开始。
多年前的两部长篇小说后,许言午停止了小说写作,“那是一段漫长的荒漠期,不知要往哪走,怎样走”。之后的十多年里,他找不到适合的表达渠道,丧失了创作热情,对文学存在的价值也产生了深刻怀疑,写艺评,做话剧,办公司,逐渐远离文学创作。“我发现自己的身心几乎完全被外部的人与事所占据,所困扰,活得很焦虑很辛苦。人活在世上总有所求,但更多时候我们在外求那些可见之物,而不懂得或忽视了求内心不可见之物。”
在豆瓣读书现有的几十条短评中,几乎无一例外都打出4星甚至5星。其中有一条这样写到:故事还没过半的时候就戳破了所谓的怀旧。野渡无人舟自横,其实横舟,也很孤单。
小说描写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扬兮镇的人们在时代潮流中生活的起起落落。以邻家女孩丁晓颜为主人公,通过她与同为小镇青年的张咏的情感线索,串联起小镇三代人、四五个家庭、十来位主要人物。青年评论家贺嘉钰认为,小说并非全然明亮,许言午写下的更是困顿、遗憾、失落、孤独和爱情的消逝,并以理解和宽宥将种种真实重新擦亮。
很多读者是一口气读完《扬兮镇诗篇》的。小说不乏世俗窠臼,许言午却无意深入探讨人性,每每点到即止,笔触凝练而审慎。鲜以夸张手法制造剧情冲突,从生活逻辑出发,情节递进淅淅沥沥渐入人心,平淡却深刻。许言午说,他不希望过于坚硬的文字冒犯读者,取名“诗篇”,亦是希望字里行间能够接续中国古典诗歌传统,隐逸克制,含蓄留白。以“白话”形式将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柔软和不屈呈现出来,就够了。
虽然《扬兮镇诗篇》以故乡小镇作为舞台,但许言午对那里一度是疏离甚至厌恶的,来北京后,他曾多年没有回老家。2017年,年迈的父亲去世,许言午第一次真切意识到,人是会离开的,是真的会不在的。对生命与死亡、对自我与孤独的重新理解,对人间世相纷繁情感的再度审视,让许言午有了言说的冲动,“在这部小说里,我还是想表达美好的东西,有悲,但是不凉”。
主人公张咏身上有着作者、也有着无数离家游子的身影。许言午承认,自己对故事里的男性角色是有所嘲讽的,嘲讽他们追虚逐妄,求而不得后又自暴自弃,变得乖戾而冷漠。正如书中所写,人到中年后,张咏才意识到,早年一味追求出人头地的狂飙突进式的人生态度,以及对待扬兮镇、对待周围的人,包括后期对待丁晓颜的偏激狭隘,是具有毁灭性的,这种毁灭性针对的恰恰是他自己。
将《扬兮镇诗篇》视为对故乡的回望,毋宁说它更是作者本人在人生旅途中“觉醒”的一次精神凝结。因而许言午告诉我,《扬兮镇诗篇》这样的写作只有一次,它无法重复,也不能被重复。起笔时,他就想好了丁晓颜的命运——她必须消失。小说描写的是一个正处于剧烈变化的年代,个人欲望野草般蓬勃生长,这种情况下,丁晓颜所象征的沉静圆融的心灵状态就显现出极为刺目的局限性,难以与周边环境相容,最后的结局也就无可避免了。
作为专业出版人,韩敬群坦言很久没读到这样的小说,“让我非常自然地回归普通读者身份,与书中的人物共情,这在近年阅读体验中并不多见。”读到尾声时,他甚至想打电话问许言午,能否修改人物最终归宿。
许言午心中,丁晓颜犹如一个理想化的存在,“是我们内心深处最柔软最自在的那一小片角落,与我们声气相通,血肉相连”。当张咏说出“她就是扬兮镇”时,他达成了与自己的和解,丁晓颜也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永久的保留与复活。至此,历经岁月打磨,许言午亦完成了他人生中的第三部长篇小说——真正为心中所想、真正自觉饱满与扎实的文学作品,哪怕已跨越二十年的漫长光阴。
对这部小说,许言午满怀尊重。他将行文结构对应成故事中的九封往来书信;巧妙设计人物对话,前后形成隐喻互文,余留意犹未尽之思。正式出版前,小说几乎没有再修改。不写作的很多年里,许言午依然保持着阅读习惯,尤其从中国古典名著中汲取养分。因此,动笔写作《扬兮镇诗篇》时,并未觉生疏,“好像只是隔了几天没写”。
如果把自己放在扬兮镇,许言午笑说应该不会出现在作者笔下,“因为太乏味了。小说里每一个有名有姓的人物,都比现实生活中的我更有趣”。性格偏内向的他很少主动表达,主动与人交往。写小说是件放松而愉快的事,因为可以独自在沉默中完成。面对人生中的改变与失去,他现在已经能够相对坦然地接受了,“或者说是随遇而安吧。这个‘安’我把它理解为心安,心安定了,就能够积极面对”。
现在,许言午正创作一部新的长篇小说。当我问及是否会成为职业作家时,他表示无法预设,按照自己的节奏,安心写下去就好了,“也许状态越来越好,也许不尽如人意,都有可能,谁知道呢。”
采访中最后一个问题,最想成为小说中的哪一个人物,许言午的回答是,越来越想成为丁晓颜了,哪怕多一点点像她也很好。
访 谈
中国作家网:你曾说《扬兮镇诗篇》是为了安放对故乡复杂、矛盾的感情而创作,为什么会产生对故乡的“无所适从”感?这种内心变化随着地理位置的隔阂与岁月时空的流转,对大多数离开故乡的人来说是必然的吗?
许言午:每人成长经历不同,个体感受不同,对故乡的“无所适从”感也会因人而异。以小说主角张咏为例,他和我是同龄人,成长年代恰逢改革开放,社会变化剧烈,人心躁动,充满各种可能性。很多年轻人有条件离开故土,去往更广阔的天地,张咏也是其中之一。但他的“离开”还包含着对故乡深刻的背叛——这点特别重要,正是后来回望时产生复杂、矛盾的感情,乃至无所适从的根源。我相信,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这种情感或多或少都有一点,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扯不断理不清,带有负疚感的“牵挂”吧。
中国作家网:作者写长篇时,往往会与人物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久久沉浸在情感中。塑造小说角色时,你会提前做好性格/命运的预设吗?还是跟随情节,人物会产生自己的骨骼与血肉,反过来引着你走?
许言午:《扬兮镇诗篇》的写作更倾向于后者。小说里的人物,除了丁晓颜,其他都有生活原型,但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而是糅合了几个人物的特征在某一人身上。在故事的进行中,这些人物会产生自己的骨骼和血肉,会有新的发展。例如苏冬丽,在小说里写到她时,我很自然地给她增加了一个细节,让她在看守太平间的工作间隙埋头读佛经。这不是预设的,也不是其原型具有的特征,只是到了此时,苏冬丽自己想读了,她有了这个心理需求。对理解该人物很有帮助,也让这个人物形象更为鲜明。
中国作家网:对主人公丁晓颜与张咏,有很多不同解读。二人相互映照,一体两面。我认为,丁晓颜如同扬兮镇,也如同离乡游子心中的故乡,安然沉静地坐落在那里。作为精神依托,她始终都会是记忆里纯然原始的样子。而张咏就像想逃离故乡的人,经历从厌恶到醒悟的回归。不知能否这样理解?
许言午:是的,你说得很准确。丁晓颜是心,张咏是身。扬兮镇是虚构的一个小镇,名字取自《诗经》。这个“故乡”也并非物理意义上的故乡。写作这部小说对我来说,是对“精神家园”的某种回归,是对美好传统的致意。人类拥有长久的记忆,这是生而为人最大的幸福之一,也是痛苦和烦恼的根源之一。人有时候需要往后看一看,才能望得更远,向前走得更笃定更安稳。
中国作家网:丁晓颜的结局,你最后的描述是“她抿着嘴,露出了笑容”。葬身于火海,但只是烟气中毒,仍保持着原先入睡的样子。虽然你曾在采访中说所描写的年代社会剧烈变化,丁晓颜必须离开,但我认为面对生活,你依旧抱有理想主义。
许言午:老话讲不如意事常八九。人活在世上,现实常常不尽如人意,但我还是愿意保持希望,留住温情,在小说里也是如此。年幼时,父母、老师就教导我们,要追求真善美,我懵懵懂懂,却是相信的。念大学时,已经将信将疑了,这个将信将疑持续了很多年。到现在这个岁数我又信了,而且是确信无疑。大致是这样一个心路历程。
中国作家网:小说写作过程是否顺利?完成后的两次修改主要是哪里,还有哪些遗憾之处?
许言午:写作很顺利,初稿完成得算是相当快了。修改的主要是一些需要相互对应的细节,将其打磨得更清晰晓畅。一部作品成书后,作者回头再去细读、审视,难免有遗憾之处,总能挑出一堆毛病来,心想我本来可以写得更好一点。写作的人都是眼高手低的,但这不是坏事,因为眼高所造成的遗憾心情,可以成为一个热情的起点,将手低的我兴致勃勃满怀信心地带入下一部作品。
中国作家网:书中的人物各有故事与结局。正如你在结尾写道:“我们总以为唐代是花团锦簇、热热闹闹的。可是翻开《唐诗三百首》,每一首都很孤单。” 你是一个悲观的人吗?如果孤独是注定要面对的处境,那么人生的意义又在何处?
许言午:对人性我基本持比较悲观的态度,包括看待我自己。与个人心性和成长经历有关,但它有很大局限,并不一定客观真实。我有时会自问:真的是这样吗?多问几次后,或许就更接近真相,体察到更多,多一层理解和包容,对人对己都是如此。重要的不是遇见什么人,什么样的处境,而是要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应对。丁晓颜和张咏的区别即在这里。《扬兮镇诗篇》就是在这样的心态下写出来的,里面随处可见个人的孤独,但它不是注定的。
 更多
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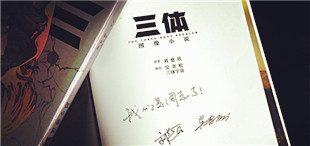
吴青松:我把画《三体》当成是一场修炼
“我把画《三体》当成是一场修炼,修炼可以为之后的创作提升能力,同时在其间隙,也能为之后的创作做好更充分的准备。”
 更多
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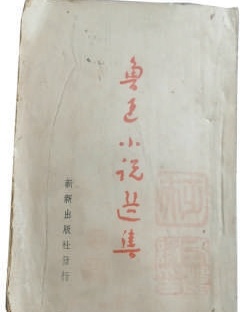
石舒清:三本书的收藏记忆
记得大概十年前,我买到一本版本很是特别的《忠王李秀成自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