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树下的迁徙》:生活气息扑面而来
从历史和现实境况而言,桑树都是极富诗意和梦幻感的植物。桑树在丝绸之路历史上曾留下古代东国公主暗传蚕种至于阗国的典故,亦有东汉刘秀在生命危急之际因食桑葚而得以活命的故事。这些都让桑树在发黄的史册中散发出光芒。
那么,在素有“火洲”之称,年降水量极为有限、植被极难生长存活的吐鲁番,桑树与诗歌之间会有怎样的关系?或者说,对本诗集作者马永霞的出生地吐鲁番鄯善县来说,桑树又是怎样的一种植物?它在诗人马永霞眼里,又具有怎样的生命和使命召唤,促使马永霞把“桑树”作为意象一再抒写、吟咏?在诗集第二辑的篇章页,马永霞引用的诗句,或多或少是一种印证:“在吐鲁番盆地,北风/会把一个人的脸雕刻得更加干净/西北腹地,空气则潜藏得很深/代替它流动的是羊群和阳光”。
吐鲁番是丝绸之路的十字路口。这片土地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交汇的重要地带。吐鲁番盆地的桑树,无论是在历史记载中,还是在马永霞的具体生活场景里,都有言之不尽的深远意境。因此,她的诗歌相比于历史或学术研究,就多了一份灵动和自由优势。比如《索取》:“你的眼睛/走不出我的眼睛/它们夺走我,把我放在/行走在沙漠的骆驼背上/如果不是你的出现/雨会一直下在我的沉默里/现在,我只想说/请离开我的视线/那样,我会一直寻找你/那样,你会一直看着我”。
马永霞的诗歌犹如庞大的桑树一样具有深远的根源。作品的根源,无论在小说、散文和诗歌中,都显得尤为重要。它会让诗歌和诗人变得可靠。也就是说,一位诗人写下的诗句,一定在字词之间潜藏着某些确切的影子——生命、家族、故乡、精神、灵魂、记忆、怜悯等,不一而足。有了这些具体的物象来源,会让阅读者寻觅到诗人从哪里来,借以诗歌表达要到哪里去。
读马永霞的诗歌,最直接的感觉是她诗歌的生活亮色和气息会扑面而来,让人感到无论快乐还是痛苦,都犹如狂风骤雨在苍茫大地上恣肆旋转,把人世生生不息的力量完全倾吐。犹记得在鄯善县的吐峪沟村,“我”曾见到一群老人成排坐在桑树下晒太阳,仔细一看便发现了有趣的一面,他们严格按照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的顺序依次而坐,绝不打乱年龄而乱坐。他们就那样坐在桑树下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什么,太阳照在他们身上,使他们显得安然从容、怡然自得。在吐峪沟的另一户人家门口,每到用餐时间,便有一位老人从大门里出来,揪住桑树枝条捋下桑葚,吃上一阵后心满意足地回屋。这样的具体场景或生存景象,在马永霞的诗中比比皆是,她敏感地将其抓住,并将其付诸笔端。譬如《桑树下的迁徙》:“古老的桑树下/一位老人头枕树荫/一汪岁月的山泉/流经他正午的梦香……”
同样的诗歌还有《暗光里的亲人》,对桑树的描写则更加确切,并呈现出“人在桑树下”的具体生活。抒情主人公写下的已不是昔日记忆,而是历经岁月蹉跎后的沉默和厚重。她从中找到生存于此的人群(也可视为诗人自己)的精神支柱。在这一刻,诗人的目光落到了实处,“出生地”或者“故乡”不再是符号或名词,而是沉淀于内心的宁静湖泊:“天空还是蓝的。春天/正以一棵树倒下的速度铺开/四周,一下子空阔了许多”。
从一棵桑树出发的并非只是人生,也许还有精神和心灵的漂泊。马永霞诗歌中的桑树,虽然很明显地附着于吐鲁番这一具体地域,但却不是单纯地依附,而更多地呈现出精神与外界(世界)撞碰后的火花迸溅,让人不仅看到诗人的阵痛,亦看到世界的复杂。这时候的诗人,因为难舍近在咫尺的心灵渴望,总是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在“故乡—心灵—外界”的反复扭结之中,心灵为之哀伤,身体为之隐痛,而生命之甘苦或个中滋味,却犹如桑树上慢慢升高的月亮,越加皎洁反而越加遥远。写作,是此时此刻的诗人获得救赎的唯一方式,即使其诗意犹如精灵一样一闪即逝,但给诗人带来的慰悦感仍然是别的事物所无法替代的。
即便如此,马永霞仍然在诗中谨慎地选择了告别。她知道,任何一种事物都会因其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必然存在“再出发”,或者迟早会在下一个十字路口与自己的命运重新相遇,所以,她小心翼翼地把故乡作为出发地,开始了另一种观望。正如罗曼·罗兰所说:“痛苦这把犁刀一方面割破了你的心,一方面掘出了生命的新的水源。田野又开满了花,可不是上一个春天的花。”从阵痛和裂变中重新出发的马永霞,身上明显带着难以割舍的根源,这让她慢慢在心灵中感受到了慰勉。在《试着飞行》一诗中,这种“旧我—嬗变—新生”的心灵变化体现得淋漓尽致:“从没经过那样的陡坡/刹车失灵的自行车上/我借着惯性,完成了一次极速俯冲/在惊心动魄中实现了飞翔的梦想”。
再比如《学习沉默》一诗,亦是诗人在命运变化下的阵痛体验:“后来,我见过众多沉默/见过从未见过自己父亲的孤儿/在眼泪中的沉默/见过女人沉陷在眉睫上的沉默/见过大千世界的沉默/而我,在学习母亲/那样沉默,那样从容”。有了这样的阵痛,生命便变得越来越具体,其内心自然会充满强大的自信和安全感。亲人是上帝安排的镜子,从对方身上可以映照自己。这首诗既有马永霞的生命体验和感悟,又有对亲人的理解。在她看来,任何时候的生存都有意义,因为不论轻松或者沉重,其实都是对生活的接纳。人活着,又有谁不在这种情况中挣扎和沉浮?
马永霞这部诗集中的作品,给人总体的感觉是细致地展现了她精神嬗变的过程,从中也可看出她的成长和为成长付出的代价。一个人走得再远,遭遇的欢乐或痛苦再多,都会被世界(命运)刻画上生命年轮。经过岁月打磨之后,最终会孕育诸多感悟和体会,让诗人不知不觉写下诗歌。
从故乡出发的马永霞,在启程的一刻也许就已经在回归。只是她出发时在凝视世界,而回归时却在凝视自己。读马永霞的诗歌,得到的感受便是如此。马永霞的所见、所思、所感,都有确切而牢固的根源,无论是抒情还是反思,都格外引人注目。马永霞的诗歌凸现出强烈的“我手写我心”的特点,她有生活,于是就有了这些诗歌。她将精神向度和心灵深度统一到了和谐的抒写之中,突出了诗歌艺术效果,亦让她的出生地、故乡和桑树,都在这部诗集中变成了证词。这种证词,是诗人与诗歌相遇时紧紧抓住的光束。
(作者系作家)
 更多
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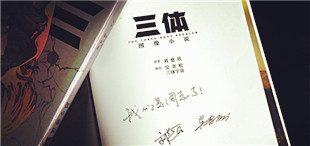
吴青松:我把画《三体》当成是一场修炼
“我把画《三体》当成是一场修炼,修炼可以为之后的创作提升能力,同时在其间隙,也能为之后的创作做好更充分的准备。”
 更多
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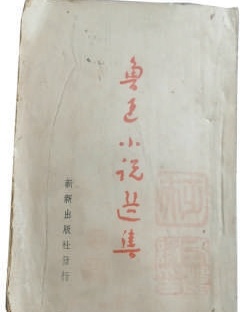
石舒清:三本书的收藏记忆
记得大概十年前,我买到一本版本很是特别的《忠王李秀成自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