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贴大地的心灵歌者——曾剑小说论
曾剑的小说可读性强,清新利落,真挚感人,充满正能量。近几年,他一直在努力拓展写作的深度和厚度。长篇小说《向阳生长》的出版,标志着他个人写作史上的一次飞跃。小说有“集大成”的意味:老家红安的竹林湾、石桥河,父老乡亲,农家孩子从军的故事,成长的困惑,以及战场上血与火的洗礼,构成他小说的血肉、筋骨、灵魂与质感,这些曾让他魂牵梦绕、泪涌不已的生命记忆,终于获得了完整而酣畅的形态。《向阳生长》的语言更加精妙洗练,故事更加曲折复杂,充满思想的张力,人物、细节和意境营造也都更加鲜活细腻,意蕴丰厚。
文学是心灵的外化,能够击中读者心灵、感人肺腑的作品,必然来自一颗真诚而有力量的心灵。《向阳生长》在击中读者心灵的瞬间,还一并点亮了曾剑的全部写作,使他20余年自谦为“蜗牛爬行一般”[1]的艺术探索显现出独特的美学底色,有了属于自己的质地与气象,所信与所向。概括起来,可称之为“紧贴大地的心灵歌者”。曾剑始终秉持现实主义写作理念,以紧贴大地的姿态观照历史与现实、命运与人生、灵魂与存在,并以强韧的心灵力量和超越性的精神指向,不断向人性与人心深处开掘,以轻快写沉重,以沉重写明亮,抒写向上的意志,重申人们心底的情义与纯真。于是,一位极具辨识度的实力派作家也随之诞生了。
一、从自发到自觉的现实主义写作
曾剑的小说创作起步于2000年,被读者熟知是在2010年左右发表《饭堂哨兵》《冰排上的哨所》《穿军装的牧马人》《循着父亲的目光远行》,以及出版长篇《枪炮与玫瑰》等军旅小说之后。2018—2020年,《净身》《竹林湾往事》《像白云一样飘荡》《我的上铺兄弟》《哨兵北舞》《乌兰木图山的雪》《玉龙湖》《整个世界都在下雪》等中短篇刊出,以及长篇力作《向阳生长》问世后,他早已成为“当代实力派作家”[2]。之后,他的创作持续喷涌,仅2021年就发表了《后现代的花枝》《三哥的紫竹林》《白鸽飞越神农架》《慈悲引》《康定情歌》《太平桥》等中短篇,2022年后,又推出了长篇《山河望》和中篇《比远方更远》《玫瑰与夜莺》《桥》《铜牙》等。在此期间,他还斩获了诸多奖项,包括全军军事题材中短篇小说评奖一等奖,辽宁文学奖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奖,方志敏文学奖等。
现实主义写作之于曾剑,既出自某种创作机缘,又是他由自发到自觉的艺术选择。起初,他模仿《解放军文艺》上面的故事,将军营里真实发生的几个小故事写进了自己的小说,采用的就是最基本的现实主义手法。之后他不只偏好于此,还越来越得心应手,并将动人的细节、独特的视角、真诚的立场视为最重要的小说经验和追求。这个时期曾剑塑造的士兵形象往往新颖别致,与众不同。他所选取的不是冲锋陷阵的高光人物,而是部队里的一些配角,甚至是一些被忽视的边缘人物,一些在某个角落里默默坚守的小小“螺丝钉”。比如,在《枪炮与玫瑰》中,他有意避开了作为朝鲜战场上的主角——战斗英雄,而是刻画了一队随军出征为战士们跳舞唱歌、加油鼓劲的文艺兵,通过展现他们所经受的战火洗礼,以及战后与厄运的顽强对峙,完成了一幅震撼人心的壮美画卷。
这样取材固然是一种智慧,但也是一种冒险。因为想要从那些边缘人物身上展现家国情怀、山河壮志,乃至崇高的军人品格,何其难也,一不小心就容易失真。鲁迅说,写小说关键在于“选材要严,开掘要深”[3]。所以,精心选材需要智慧,如何开掘则更加考验作家的功力。事实证明,曾剑是经得住考验的。首先,他的小说人物在现实中都有原型,在他们身上寄予了作家的真情实感。其次,小说所要表达的一切,必须依靠细节来推动和落实,所以凭借扎实的细节刻画,作家的创作意图得到了实现。比如,《饭堂哨兵》写的是一个训练有素、军姿笔挺的警卫战士,整日在机关食堂门口站岗。这篇小说的视角新颖,容易出彩,而且这个形象有原型和作家的真实体验。此外,作家对小战士心灵世界的开掘也十分精细到位。首长们每天都从他眼前走过,但几乎没人注意过他,这将引起怎样的尴尬与孤单?他后来内心又经历了怎样的波澜与成长?他作为军人的价值感和荣誉感从何而来?他的故事能否触动对现实的反思和批判?这些问题在小说里都有细腻且颇具深度的呈现。小说的细节刻画也相当动人,既令人难忘,又引人遐思。如结尾处尤为感人,没人知道哨兵的名字,他自己最终也没说出自己的名字,但随着他给自己下达的这道命令,可怜的小哨兵已不再纠结,而是喊着“我是哨兵,饭堂哨兵”,并郑重地“挺胸、抬头,收腹,提臀,两腿绷直,两眼平视前方,把自己站成一个标准的哨兵”[4]。
当然,在曾剑服兵役期间,作为部队专业作家,军旅小说的写作范式也强化了他的写作思维。“‘现实主义’始终是军旅长篇小说自觉遵循并积极倡导的文学观念和创作方法”“也构成了军旅长篇小说最为核心的叙事伦理、审美范式和风格底色”[5]。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曾剑的职业身份和这种较为特殊的写作伦理,使他一直走在现实主义写作的路上。
2017年年底退役后,曾剑完全可以有所调整,尤其是当他再度进入鲁迅文学院与北师大联办的创作研究生班深造,师从精通现代主义的作家苏童,成为马尔克斯的追慕者后。但从稍后的创作来看,他不但没有放弃现实主义,反而更加自觉地坚守着。此时他的创作不仅加强了写实,还“从多方面指向传统”[6]。很多作品无论是从词语、句式,还是从语感、味道、意境上看,都明显散发出古典的韵味与美感,带有地域性的色彩。比如《向阳生长》的开篇:“日头挂在河西坝,霞光涂抹下来,竹林湾像一幅油画。大人在畈田忙活,细伢还没放学,二奶成为画中的主角。她扶着门框,跨过门槛,下了三级石头台阶,倒腾着小脚,在温暖的光线里。蹒跚走向后山坡。二奶老了,身子越来越短,影子越来越长。”[7]写小说,当然是写故事,但说到底,也是写语言,语言考究是作家的美德。作为文学之一种,小说自然也是语言的编织物,有怎样的语言,就有怎样的美学追求。现实主义写作对语言的要求是要符合现实的逻辑,与真实的生活相匹配,要求扎实、精炼与传神。韩春燕认为《向阳生长》在语言运用上很成功,这部小说“到处闪烁着像钻石一样光芒的句子……诗意自然,非常具有美学韵味”[8]。另外,从情节设置、人物塑造、细节描写等方面,我们也能明显发现曾剑小说的写实深度和力度都有大幅提升。因而,当进一步解读这些作品时,我们就不得不重新打量作家的小说理念,进而思考和判断其中可能包含的重要价值。
二、紧贴大地与心灵掘金
进入21世纪之后,在市场化、大众化和消费化的时代氛围里,小说家们对于文学的认识已变得清醒而成熟,态度也变得较为通透和从容。是继续走实验主义路线或重拾现实主义,还是走通俗、网络、类型小说路子,抑或是尝试将它们兼容起来,艺术和市场两不误,成为摆在作家面前的选择。当然,一切无所不可,一切也可能变得茫然无措,很难找到坚实的方向。但是,诚如里尔克所说,“创造者必须是一个完整的世界”[9],所以对于任何一位有抱负的严肃作家而言,仍然要努力为自己的创作找寻坚实的方向。对于曾剑而言,亦是如此。
那么,究竟如何去找?方向在哪里?作家们当然各有探索。而就曾剑而言,我认为他成功地找到了两个方向:一是要“紧贴大地”,即坚守现实主义写作,紧贴真实的生活经历,从自己最真实的、最具个性化的生命体悟里寻求小说的思想性与超越性;二是追求一种综合和平衡的小说技巧和艺术效果,以达到某种意蕴丰厚的小说境界。
曾剑是一位比较依赖个人经验从事创作的小说家,应该说这是他的局限,因为容易限制想象力和创造力的飞翔。但换个角度看,这也造就了他小说的个性与深刻。“无论世事多么艰难,总有阳光透过云雾,照耀人间。”这不仅是他在《向阳生长》腰封上写给读者的一行金句,也是从他最真实的生命里结出的思想的“金疙瘩”,从中可窥见曾剑内心的某种自觉与坚定。作为一个从偏僻山村走出来的军旅作家,他的人生经历必定曲折艰难。可是,曾剑给人的感觉尽管也有沧桑感,甚至苦难感,但更多的却是温暖与感动,他心里总是热的。据他讲,当年他的老父亲,无论怎样含辛茹苦,也要把细伢们一个个往外送,盼他们跳出农门吃外饭,光宗耀祖。可以说,没有这份伟大的父爱,就没有曾剑的今天。同时,这还使曾剑对那种强烈改变命运的“向上的意志”刻骨铭心,他从小就继承了家乡的红色血脉,有了保家卫国的军人情结。故乡竹林湾那片土地上的亲人和乡亲们,也给了他无限的温暖和关爱,让他后来无论走到哪里,无论见识多少世态炎凉,多么扭曲或险恶的人性,都始终愿意相信人们心底的善良与纯真,相信人与人之间总会有情义与温暖存在。绿色军营里的首长和战友们,也给过曾剑许多美好的情感记忆,他们的鼓励和厚爱支撑他在艰苦的磨砺中,逐渐成长为真正的军人和男子汉,心中有了家国和山河。
于是,当他“紧贴大地”,从生命的根基里去寻找某种值得坚信的精神价值与力量时,曾经温暖过他的缕缕“阳光”,自然成了他的所信与所向。而故乡与军营,也就成了他最主要的创作题材。这种由生命实证带来小说观念觉醒的过程,恰如沈从文对故乡边城,以及“乡下人”那把尺子的重新发现。如果说,当年沈从文用心描绘湘西人的古朴自然,是为了提出一种向人类远景凝眸的理想[10],重塑民族品格。那么,如今曾剑这样不断地书写“阳光”,则是为了表达一种向人类美好心灵回归的理想,重唤当代人心底的情义与纯真。
因此,在“向阳”时期及之后,沿着这个方向,曾剑写出了很多佳作,比如《循着父亲的方向》《竹林湾往事》《净身》《像白云一样飘荡》。它们长长短短,共同书写了一部家族史、乡村史、个人成长史和精神史,体现了作家对历史与现实、命运与人性的整体观照。同时曾剑还成功塑造了一系列鲜活、丰满的人物形象,它们彼此辉映,充分显示了作家创作的深度与厚度。作家透过这些人物及他们的悲欢离合,完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人生与人性画卷,更唱出了一曲感人肺腑的心灵之歌。其中塑造得最为成功的,也是最令人感动、无法忘怀的人物,当属聋二。韩春燕曾谈道:“聋二是《向阳生长》里最光彩的人物,也是典型化的人物,甚至可以说是对当代中国文学史的一个贡献。”[11]聋二原名刘满堂,是竹林湾里的一个寡汉条子。他独自住在北山洼上,靠做砖坯瓦坯糊口。他整日沉默寡言,被人欺负也不吭声,也不近女色,好似一个孤僻清高的怪人。作家用深情的笔墨、精心的悬念设置和高超的叙事技巧,一点点将他伟岸的人格树立起来。小说采用第一人称,以四郎的口吻开始讲述:“我”有6个兄弟,从小因为家里太穷,母亲就把“我”外给,可那年头谁都不想多张嘴,不过聋二竟二话没说收留了“我”,这让“我”和母亲都很感激。后来,“我”发现他很不一般,他有文化,爱干净,乐善好施,只是有时行为有些异常,每次抹汗如厕时总是遮遮掩掩。不过,他对“我”比亲生父亲还好,总是无微不至,教育“我”既耐心,又不失严厉地敲打。更重要的是,他总是倾尽所能培养“我”,省吃俭用地供“我”上学,给了“我”一个将军梦。最令“我”感动的是,当“我”入伍出现岔头时,为了争取名额,他竟然豁出去在负责招兵的领导面前,将他最在意的裤子脱掉,赤条条示人。“我”当时就站在他身后,并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是什么让招兵的同意带“我”走。之后,他更加呵护着“我”,如同呵护着一个最美的梦。每当“我”犯浑胡闹时,都有他愤怒的身影;每当“我”回家探亲时,都有他关注的目光。后来,“我”成为军官在部队过上了好日子,他在我心中也逐渐淡去。恰在这时传来了他病危的消息,“我”惭愧地赶忙去看望,可惜为时已晚,他见完“我”最后一眼就心满意足地走了。他的遗嘱是只留“我”一人在身旁,为他做最后的净身。当“我”解开他的裤子,看到一张秀姑的照片,又读到留给“我”的笔记本后,才得知他深藏多年的秘密。原来他早年上过前线,虽说死里逃生,但在一次极其惨烈的战斗中身负重伤,炮火炸残了他的“命根子”。可是后来,这个不幸的男人没有退却,反而更加视死如归,主动投入更多的战斗,并且“无情”地拒绝了痴情的恋人秀姑。再后来,战争结束后他回到竹林湾,一直隐忍地活着,再次“绝情”地拒绝了他深爱的秀姑,而将全部的爱和心血都倾注在“我”身上,将一个贫苦人家的细伢子培养成了一名光荣的军官,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到此,聋二的情深义重,聋二善良与伟岸的人格,将小说推向了高潮,也完成了小说在思想与精神上的超越。
情深义重历来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主要的价值观念之一。儒家思想始终推崇仁义,力图将之从家族血亲推及整个社会。经过宋明理学到了阳明心学,儒家哲学甚至认为人的生命情感才是真理所在,人类的真理不在别处,就在人们的良知中,在亲情、友情、爱情和民族大爱中。毫无疑问,无论社会如何发展,善良与情义仍是人们心灵中最柔软的所在,也是精神世界里最强韧的部分,有着永恒的价值与意义。我们每一个人,“总是在自我保存和自我实现的过程中达成幸福的”[12]。而在自我保存和自我实现的过程中,任何一个“小我”都离不开“他者”,离不开亲人、友人与贵人的支撑与温暖,更离不开“大我”、整个社会,乃至国家民族的庇护与孕育。在小说世界中,聋二的善良和对四郎的爱是真诚的,四郎对聋二的感激也是发自肺腑的,人与人之间有着真实的情义。在现实生活中,竹林湾和军营给予曾剑的培养与温暖也是事实,他对故乡与部队的感恩也是无比真诚的,这构成了作家心灵中最强韧的力量。从这个角度上看,曾剑小说所蕴含的善良与情义书写,不仅提升了作品的思想高度,还成功地践行了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因为讲好“中国故事”,就是要讲好中国人心灵的故事。
另外,曾剑这种充满阳刚与力量的书写,对于弥补目前中国军旅文学创作中存在的不足,也有重要的价值。李敬泽曾尖锐地指出,近30年来,军旅文学中的某些套路和特点需要严重反思,比如过于表现人性化,可是“好像只有那些琐碎的、软弱的那才叫人性,那么崇高的、有力量的那就不叫人性吗?”傅逸尘也坚持认为,如今应当“强调和重建英雄叙事”,追求一种“崇高的阳刚的文学审美理想”[13]。
那么,从这两个角度看,《哨兵北舞》《我的上铺兄弟》《山河望》《比远方更远》同样也是纯正的中国故事和充满阳刚之气的英雄主义叙事。这些作品中,有为了成为真正的男子汉而放弃“北舞”、自愿到艰苦寂寞的边防去锻炼和扎根的舞蹈系大学生韩泽中;有为了改变命运和军人梦而考入军校或直接入伍的一群农家娃,如赵多、王守富、罗厚兵、马德礼、周善仁、乔大宝等;还有从穷乡僻壤的穷孩子成为士兵,后来在边远地区基层公安战线上壮烈牺牲的英雄李大林。这些作品共同构成了一部“军营心灵史,青春励志书”[14]。我认为其中最吸引人注目的当属那群农家娃。作家用轻盈明快、风趣幽默的笔调,既写出了他们的小斗嘴、小使坏、小心眼和小色胆,也写出了他们之间真诚的帮助与鼓励,以及真挚的情义与温暖。他们虽然出身于社会最底层,承受着物质的匮乏和见识的贫瘠,但充满了青春的元气和正能量。这群阳光的军校小战士,不能不使人相信“广布在大地上的中国元气所在,贫瘠的土壤同样能孕育钟灵毓秀的种子”[15]。由此,这些“向上”的书写,还很好地起到鼓舞民心的作用,对于扭转当下某些不良的创作倾向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三、综合与平衡的小说艺术
当然,曾剑的小说虽然“阳光”充足,但也从来都不缺少阴影和沉重。一方面,作为严肃的现代小说,问题意识和批判性是不可或缺的内容;另一方面,就真实性和深刻性而言,无论观照历史与现实、命运与人生,还是灵魂与存在,任何作家都必然要触及阴暗的部分,只是在具体的艺术处理上不尽相同。这就说到了曾剑小说的综合和平衡的艺术。借此曾剑不仅将小说的可读性与严肃性、朴素与诗意混合起来,将历史观照与现实批判、虚构与现实结合起来,也将人物命运中的不幸与希望交织起来,将人性与人心的阴影与光明调和起来,并达到某种恰到好处的平衡,起到以轻快写沉重、以沉重写光明的独特效果,给小说带来恢宏的史诗气质。
如果仔细看,曾剑小说里的阴影和沉重何其多也。饥饿贫困、物质匮乏、鳏寡孤独、愚昧落后、阶层固化、盘剥压榨、人性被权钱扭曲、环境被污染等,遍布各个角落,构成了人物性格的来源和叙事的动力。在“竹林湾系列”中,正是因为贫困,桂花嫂才把四郎往外给;在“军营系列”中,正因为家乡缺水,守卫的海岛上也缺水,李大林才晕水、惜水如命;在《午夜飞翔》里,正是为了讨回应得的薪水,一个农民工才被逼得以死相搏。可见,曾剑的小说里不是没有阴影和沉重,只是通过综合和平衡的技巧,作家将他们巧妙地织入了轻快的叙述中,使之变成小说里一个个好玩儿的、不断反转的故事。这样的处理不仅将阳光与阴影由表及里地交融为一体,也避免了许多底层写作常见的问题,就是一味展览苦难与不幸,而缺少思想与精神的超越。周景雷说:“真正的超越性写作,不是不关心苦难和弱势的呼号,而是能够从对这些的俯视中获得某种精神超越。”[16]曾剑的小说创作就属于这种超越性的写作。
另外,在刻画人物内心世界时,这种综合与平衡艺术的运用,也使曾剑笔下的人物变得更加真实生动,立体丰满,富有层次。作家不仅将人的兽性与神性交织起来,浑然一体地演绎出来,还在某个平衡点上,让深藏于人们心底的情义、大爱与纯真等闪光品质,真实自然又有力地生发和彰显出来。比如对于聋二伟岸人格的塑造,就得力于此。作家先是在小说开头伏线千里,然后在中间不断暗示,最后在结尾处精心设置了两个人物,即救护和照料他的女护士艾文和身负重伤的小林子,然后通过综合与平衡之术,借由这两个年轻生命的突然消逝所带来的生命触动,将聋二由平凡到伟岸的复杂而真实的内心世界,完整而说服力地呈现了出来:“我总是冲在最前面,我真的不是那么伟大,我只是想死”“我活着,好像就是为了怀念她,艾文,还有小林子,还有你秀姑,当然更是为了你——四郎向阳!”[17]
当然,坦率地说,曾剑的小说也并非总是将综合与平衡处理得这么好。有些早期的作品,确实略显单调和模式化,比如结尾变化不多,总是一味扬上去;写眼泪也有些多,总是讲一段故事,一行眼泪,不是涌出来就是泪流满面,缺少节制之美。
不过,曾剑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些问题,最近几年他不仅对此有所节制,还努力地在拓展着自己的写作。周建新说:“曾剑近年的创作有了根本性的转变,转变的标志就是他对人的内心的挖掘,对生活本质的挖掘,对美和丑,对真善美、假丑恶这种复杂的东西融合在一起的表达,因而越走越深,越走越远。”[18]的确如此,翻阅《慈悲引》《玉龙湖》《三哥的紫竹林》《午夜飞翔》《武湖梦》《后现代的花枝》《整个世界都在下雪》《玫瑰与夜莺》等作品,明显能看出他做了很多稳健的拓展。曾剑虽然主要还是写竹林湾和军营,还保持着故事的可读性和平衡感,还是“总是和情有关”,如孟繁华认为他的《桥》是2023年感动读者的好作品之一[19],但他已开始尝试描写都市,描写乡村振兴,涉及养老、扶贫等一些新题材。其中最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他的故事不再那么清澈,而是由书写“阳光”向呈现更为复杂、深邃而隐秘的人性和心理世界拓展。比如,同样是写篾匠三郎,《三哥的紫竹林》刻画的重点与《向阳生长》明显不同,不再讲他入赘师傅家过小日子,也不仅记录乡村手艺人的衰亡[20],而是侧重挖掘他隐秘的性心理疾患;《慈悲引》写出家当和尚的六郎,主要意图是写他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玉龙湖》讲述一位老人溺爱败家子儿子,引起女婿的不快和不解,然后故事不断反转,但最后小说并未止于对儿子身世复杂的揭秘,而是将落脚点放在了老无所养的痛点上,最终老人走投无路,选择了投湖自杀,带给读者难以名状的沉重。
曾剑的这些拓展之作,无论是在思想内蕴上,还是小说手法上,都表现得更为成熟和圆融,也增加了小说的深度和厚度。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拓展的同时也要考虑辨识度的问题。如今像他这样写“阳光”写得好的作家或许不多,但偏重写复杂、写隐秘、写幽深的作家,却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所以,曾剑在增强小说的深度和厚度时,最好能坚持好自己“紧贴大地”的姿态,继续以生命的真实和真诚去感染读者。毕竟正如他的恩师苏童所强调的,“作家需要审视自己真实的灵魂状态”“真诚的力量无比巨大”“小说是灵魂的逆光,你把灵魂的一部分注入作品从而使它有了你的血肉,也就有了艺术的高度”[21]。如此,期待着曾剑能将他的小说艺术推向一个新高度。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2年度辽宁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后文明时代’与‘文学本体论’视域下中国当代作家的文学批评研究”(L22BZW010)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迟蕊,沈阳大学师范学院教授,辽宁文学特聘评论家。
注释
[1]曾剑:《作家现在时》,《小说月报》2021年第1期。
[2]邱华栋:《序》,曾剑:《向阳生长》,第1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0。
[3]鲁迅:《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鲁迅全集》第4卷,第37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4]曾剑:《饭堂哨兵》,《玉龙湖》,第70页,济南,济南出版社,2019。
[5]傅逸尘:《“强健而充分”的现实主义主潮——军旅长篇小说70年整体观》,《中国艺术报》2019年9月13日。
[6]贺绍俊:《在坚守创作中奉献时代(记·艺2020)——二〇二〇年中国长篇小说一览》,《人民日报》(海外版)2020年12月31日。
[7]曾剑:《向阳生长》,第1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0。
[8]韩春燕:《曾剑向阳生长:一棵向阳生长的树》,引自https://www.chinawriter.com.cn/n1/2021/0105/c405057-31989554.htm。
[9]〔奥地利〕里尔克:《给青年诗人的信》,第18页,冯至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
[10]沈从文:《给一个青年作家》,《沈从文全集》第17卷,第320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
[11]韩春燕:《曾剑向阳生长:一棵向阳成长的树》,引自https://www.chinawriter.com.cn/n1/2021/0105/c405057-31989554.htm。
[12]杨立华:《中国哲学十五讲》,第1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13]中国新闻网:《“新生代军旅作家”面面观推出深度梳理军旅文学》,引自https://www.chinanews.com.cn/cul/2018/10-11/8647547.shtml。
[14]高海涛:《军营心灵史,青春励志书——关于长篇小说山河望的思考》,《鸭绿江》2022年第13期。
[15]刘大先:《贞下起元——当代、文学及其话语》,第233页,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22。
[16]周景雷:《文学与温暖的对话》,第65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10。
[17]曾剑:《向阳生长》,第420-421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0。
[18]只恒文:《曾剑:一棵“向阳生长”的树》,《中国青年报》2020年8月22日。
[19]孟繁华:《文学意味着什么——从阅读经验看文学性》,《文艺争鸣》2023年第3期。
[20]郑润良:《附录:自叙传、农家军歌与战争创伤叙事——读曾剑长篇小说向阳生长》,曾剑:《向阳生长》,第427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0。
[21]苏童:《小说是灵魂的逆光》,第12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更多
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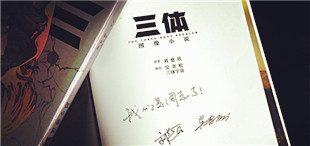
吴青松:我把画《三体》当成是一场修炼
“我把画《三体》当成是一场修炼,修炼可以为之后的创作提升能力,同时在其间隙,也能为之后的创作做好更充分的准备。”
 更多
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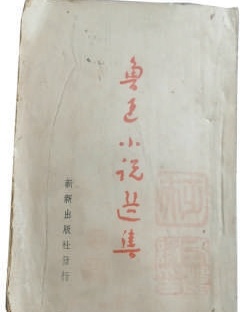
石舒清:三本书的收藏记忆
记得大概十年前,我买到一本版本很是特别的《忠王李秀成自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