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时代,人文如何避开知识的陷阱?
如同我们强烈感受到的那样,2025春节到来之际横空出世的DeepSeek(深度求索)再度将人工智能这一话题送上热搜。它以传统大模型5%~10%的成本实现与ChatGPT相当的性能,并通过开源模式推动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普及并由此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然而,技术的升级并未缓解人类对自我存在意义的焦虑,反而加剧了社会分化与个体异化。技术突破推动社会加速转型,我们的价值观、人生观以及生活方式不免受到冲击。应该说,这是科学与人文在AI时代的新一轮遭遇战,它再次迫使人类重新审视人生的意义、创造的价值与自我的边界。
事实上,科学与人文的关系是人类发展史上一个聚讼不断的命题。究其实质,这也是一个关乎工具与文明的问题。人的进化一开始就伴随着工具进化,从上天入洋的航天航海神器到日常生活的高铁飞机,都是人类心量无限放大、手臂不断延伸的标志。以书写方式的转变为例,从旧石器、新石器的标划到兽骨龟壳的刀刻,从近代以来的鹅(毛)管、毛笔到自来水笔书写,从活字印刷到机器印刷,从打字机到打印机,从手工书写到电脑录入,从电脑输入到AI生成,凡此种种,无一不彰显了工具的进化。工具的发明是人类进化的标志,但如何使用工具则是衡量人类文明与否的价值尺度。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现如今的战争使用的先进武器对人类的屠杀与伤害一再证明了这一点。在人工智能成为热门话题的当下,一个更为现实且迫切的拷问也再度摆在我们面前:人文在智能超强的AI时代需要有怎样的操守或说坚守?
一、错觉:一个由来已久的话题
如果说这次以“科技”作为前锋的AI与人文的紧张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狼真的来了”。不过,人文学者的态度却有着从自危的紧张、提防甚至敌对到接受、拥抱以及融入的转变。在这个改变背后,折射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心态:知识的获取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赢得了解放。如同高铁将人类的旅程缩短、汽车作为代步工具让人从鞍马劳顿中解放出来一样,人文学者以轻便快捷的方式将自己从浩如烟海的资料查询中解救出来。但同时也带来另一方面的问题:作为知识载体的人文学者的神圣性也随之消解。“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28年第1期)让位于人工智能。倾尽毕生精力依靠记忆积累的所谓学富五车的美誉瞬间黯然失色。人文知识分子的那一点仅存的资本和斯文一夜间通胀。
应该说,对坐拥知识的人文学者来说,AI加持下知识获取方式的便捷可谓“一则以喜一则以忧”,由此也带来了新一轮的两难或说吊诡。这涉及到一个关于知识之认知的观念问题。作为知识的载体,知识分子的心态一直秉承着这样一个不言自明的传统:知识占有的多少是衡量其学术地位和社会价值的标准。换句话说,知识就是力量,在某种情况下更是权力。
关于“知识”的垄断,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焦点问题——“文白之争”——就是一次较为明确的题解。当年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思想先驱将白话文作为催生社会转型的机轴和支点,其出发点之根本乃是打破不平等的知识分享固存结构,为普天下大众营造一个人人平等的机会和权益。1920年春,陈独秀应邀在武昌文华大学的一次演讲道出了其中的原委:“德谟克拉西”的“时代精神的价值”在政治、经济、社会、道德意义上各有寄托,那就是“反对一切不平等的阶级特权”,而具体到“文学的德谟克拉西”就是以“白话文”作为撬动这一“阶级特权”的杠杆(《我们为甚么要做白话文——在武昌文华大学讲演底大纲》,《晨报》1920年2月 12日)。不难理解,AI时代的到来不能不让我们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尽管知识的积累可能与天赋、身世、机遇以及勤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人工智能的冲击也会在势不可挡的破发下让“知识”的分配方式面临重洗的格局。
回到当下AI带来的挑战,“人文”的焦虑更多的还是重新演绎过去的故事。存在感和危机感在根本上还是主体性式微或说边缘化的问题。除却人文学者和学科的尊严、地位受到冲击之外,更为迫切和现实的问题则是人文从业者会不会被日益发达的人工智能所取代。其实,这里依然暗含着一个对知识的认知问题。当对知识的占有成为判断人才水平高低与地位尊卑之际,一种非我莫属的垄断心理便会油然而生。毕竟,坐拥知识的多少以及由谁占有是话语权力和资源配置的基本杠杆。由此产生的等级切割和阶层分化也在所难免。这样一来,我们就需要换一个视角来思考问题:当下人文的困境是来自AI还是人自身的认知误区呢?不必讳言,如果要化解人文自身的困扰,走出这一作茧自缚或说庸人自扰的局面,就需要来一次彻底的“洗心”:作为工具的知识乃是天下所有人的“公器”。在知识的获得上,人工智能让普天下的每一个人都有了史无前例之知识的最大化(占有权)的可能。作为共享的知识,在最大化实现平等的前提下,占有或说坐拥的多少已经不是判断或衡量一个人价值与尊严的关键性指标,今天的人文知识分子如果要赢得社会的尊重和业界的地位,那就要有一种跳出过去窠臼的勇气和担当,以“功夫在诗外”的心态寻找本来就属于自己却一直被湮没的心灵“绿洲”。这个“绿洲”以创造价值与意义作为旨趣,以道义、良知作为向度。不言而喻,AI时代的到来让人文知识分子生逢其时,在适得其所后安身立命。就此而言,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机遇与挑战并存。
二、错位:知识与人文的缠绕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以“你想多了”作为一句调侃的话儿。若是用在AI时代的人文学者那里也有几分道理。当我们翻来覆去、喋喋不休地为AI时代的到来平添一层如临大敌的“杞忧”之后,其实这种自危和自扰并不是一道过不去的坎儿。
承上所述,对知识的工具性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且日用不知。但如果深究,知识与人文二者虽有属性上的族谱关系,作为工具的知识与作为价值的人文却不是一回事儿。具有强烈仁道情怀的孔老夫子曾经以“伤人乎”的发问赢得了世人的尊崇(《论语· 乡党》),他那“君子不器”的定语更是对这一观念的衍发(《论语·为政》)。君子,也就是具有人文情怀的士人,不应该是僵化、教条、死板的摆设,由此才能具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情怀与胸怀(《孟子·滕文公》)。如果君子像器具那样,直愣愣地杵在一个地点,就会失去道义精神,甚至还会滋生偏狭、短视的一己之私。关于这一人文常识,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中也有异口同声的话外之音。作为非人化的器物与有血有肉、懂得人情世故的人不可同日而语:“前者只能称为驮着圣器的驴子,后者才是真正神圣的事物。人们在前者身上看到了神性,他们被赞赏,并顺从地工作;而在后者身上,人们却看到了真正卓越的人性。”从事文艺复兴研究的意大利学者加林在此借用思想家乔尔丹诺·布鲁诺的话说出了“像罐子和工具一样会说话的和工作的人”同另一些被称赞为“伟大的设计师和能工巧匠”的人之间的对立([意]加林:《意大利人文主义》,李玉成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04页)。阿拉伯有句谚语叫“驮经的驴”,比喻一头驴的身上驮满了经典,但是它却不能真正地吸收经典的知识,它只是一个载体,它的知识有益他人,而对自己毫无益处。人们借此讽刺那些有经不识经和不遵经的人。正鉴于此,接彼得拉克号称文学为“心灵的文化”之踵,阿尔丰索将这位“文艺复兴之父”的文意进一步发挥成“一位不懂文学的国王就像一头戴着王冠的驴”(《意大利人文主义》,第6页)。“罐”“驴”“器”这类东西可以是文化的承载之物,但它永远只能是工具,难以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的人类相提并论。
毋庸讳言,知识具有与生俱来的混沌性,说到底它们“本是同根生”。随着人类社会认知的发展,知识的不断两分(乃至多分)渐行渐远。于是也就有今天我们所说的知识之工具性和人文性这一“剪不断”的双栖性。进而言之,作为寻求“人事”的人文与作为探究“物事”的(科学)知识尽管在求“真”上高度一致,但毕竟还有“善”“美”一层意念上的落差。如果说“真”“知”为科学的立身之本,那么这些饱蘸“情”“意”的“善”“美”才是其质的规定性。换句话说,这乃是人文所以恃才傲物的根本,也是人文的看家本领。
人文关怀是一种深沉的淑世情怀。《诗经·小雅·小旻》中道出了人类数千年的初心:“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人文中还有着文乎其文、古奥典雅的十六字真经:“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尚书·虞书·大禹谟》)这或许正是先人、今人乃至后人化解一切荆棘泥泞、坎坷险阻的不二心经。因此,如同笔者曾经感受到的那样,面对猝不及防的AI,我们“可以如临深渊,但不可以如临大敌”(张宝明:《AI时代:“科技”不能辜负“科学”》,《中国科学报》2025年3月21日)。“深渊”意识告诉我们需要与时俱进、谨慎小心、调适有度;“大敌”意识则可能因置之不理、拒之千里为时代所弃。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从此前的冲突、提防乃至拒绝到今天的认同、拥抱乃至融入,人文学者这一态度的转变可以说是“幸会”。
三、错爱:人文与“人智”的对视
在人文与“人智”打得不可开交的今天,两者的耦合性会越来越紧。在AI给予人文更多赋能的今天,人文应有怎样的赋能加持AI则是每一位人文学者不可回避的问题。即是说,AI的日新月异使得未来一切皆有可能。在这个充满不确定的时代,有一个基本的向度却是亘古不变、一以贯之的,那就是“心”之归属或“道”之所向。如果站在人文的视野看这样一个加速转型的时代,那么我们最动情的表达应该如是说:“我心依旧。”这四个十分抢眼的字一度作为《泰坦尼克号》主题曲被反复吟唱。移至于此,它俨然就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一则隐喻:在淘金热的“资本”浪潮中,人类搭乘的那艘彰显着强大工业文明成就的巨无霸“工具”随时可能因为方向的失舵而被“冰山”或“暗礁”击碎。所谓的“坚硬”的东西,在看似无形的“上善”(若水)之“大道”(无形)面前都显得是那样苍白、脆弱而无力。
过去,我们曾经以“知识爆炸”来形容铺天盖地的信息、数据带来的冲击。今天,当我们再度被海量的“知识”包围之际,人文学者的根本命题还在于,在“道”与“技”面前人类的主体性能否经受住考验。AI时代,悠悠万事,唯此最具挑战性:这是一个关乎灵魂拷问并需要良知作答的选择题。
应该看到,在“芯片”与“心灵”之间,“芯”是“术”(即“技”或“能”),“心”是初心,是人文传统中的“道”心。众所周知,尽管“由技入道”或说“技进乎道”是中外概莫能外的事实,但“道”尊于“技”则又是中西人文的一个基本面相。“从道不从君”(《荀子·臣道》)、“道不远人”(《中庸》)、“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等等道体之说妇孺皆知。
然而,曾几何时,将“道德文章”捆绑在一起的说法每每将人文的质素湮没于知识之下。在“道术”未裂之前的古典时代,苏格拉底、孔子在与弟子的对话中关于“道德学问”一体化的表述就已经为这一暧昧关系埋下了伏笔。无论是“美德即知识”还是“尊德性而道问学”都蕴藏着知识与伦理的根亲关系。人格(人文)与学问(知识)的张力是随着人类的不断认知而发生改变的。当丈量文明的标准最终落脚于价值判断的点位之后,知识和良知之间的拣择命题才有了全新的意义。应该看到,知识的多少固然昭示着人类的文明的步伐,但是很多时候知识的快速攫取却让灵魂落魄。反观人类发展史,知识的确定性并不意味着人类进步或说文明的确定性。文人如果只是充当了知识的载体,即使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也只能是一个僵死的器物、驮经的驴子或被奴役的工具。知识作为一种工具,既可以为正义的事业服务,也可以为邪恶的行为效力。如上所述,文人并不意味着人文,知识也并不代表人格:“知识内存的多寡与具有正义、高尚、独立之气节的人文性不一定成正比。在某些特定的历史状态下,也许事与愿违。”(张宝明:《失去砝码的天平——思想史书写的尴尬》,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进一步说,在知识看似具有确定性的同时还潜存着不确定性。这一方面是说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人文学科“一切具有不确定性,而不是具有确定性;科学的最终发展不是简单化,而是对复杂性的阐释”([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知识的不确定性》,王昺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页)。在这样一种情形下,缺乏定力的知识分子往往会被“知识的不确定性”所左右以至于在理性的钢丝上东倒西歪。另一方面是说知识作为一种不确定的存在,它的内涵与外延随时可能更新。尽管人类可以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不断索取与拥有,但这样一个迫使自然与社会交出自身奥秘的探险却是永无止境、难以穷尽的。而且随着知识的增长,人类越发感受到未竟的空间在无穷扩大。这也是人类关于知识的悖论:随着有知边缘的扩大,无知的边缘也随之扩张。于是,如同黑洞一般的知识领地让人不能不产生望洋兴叹、高山仰止的感喟。对此,哈耶克曾给出这样的结论:人类追求或说需要自由的理由是因为我们无知,三个臭皮匠不一定就顶一个诸葛亮,因为“很多无知的人相加不是更加聪明,而是更加无知”([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册,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如同民主如果单以数量为凭很有可能造成冷暴力一样,知识的膨胀与发酵也可能会以冷暴力的形式让人类产生如坠深渊的无力感。这不是幻觉,而是幻灭。事实上,今天受AI情势所逼的一代年轻人已经对这个世界的真实感产生了怀疑,这不能不说是与潜意识中对“知识”产生的错爱有关。
回到本论,AI时代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随之而来:如果人类在行进过程中陷入知识的瀚海不能自拔,那就无异于泥牛入海。这是一个涉及知识依赖的命题。这一次的“知识越多不一定越不反动”不是知识带来的,而是人类自身的错觉引发的。其实,人类进化过程中面对“工具”的冲击已经有过关口前移的警醒与警示。作为知识获取过程中的“工具”发明与援用是必要的,人类不必为此大呼小叫:“每一巨大的工作,如果没有工具和机器而只用人的双手去做,无论是每人用力或者是大家分力,都显然是不可能的。”([英]培根:《新工具》,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序言”第3页)与此同时,作为工具的使用者始终要耳提面命自我:作为主体的人类在左右逢源之际千万不可异化为依赖性的奴隶或被奴役为受其牵制的俘虏。不然,在时代大潮下,我们人文学者只能束手就擒或自怨自艾。
在即将结束我的演讲之际,我更想说的是,人工智能的到来为人文的意义创造与创新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这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挑战。问题的关键不是AI是否能够取代人类,而在于人类能否见“机”行事、顺势而为。事在“人”为,AI的意义在于每个人都可以从被迫的劳动中解放出来,更自由地思考生活和意义,培养健全而自由的人格(胡翌霖:《手握AI的人类,未来不再是“牛马”,然后呢?》,《中国科学报》2025年2月21日)。只是我们要提防AI的深度伪造给人带来的知识幻象,提防因长期使用AI生成内容而在复杂问题解决中的认知依赖风险。归根结底,在“知识就是力量”的赋能下,我们还有着“良知才是方向”之人文终极关怀。
(作者系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院长。本文节选自其在2025年3月13日在武汉大学珞珈史学讲坛上的演讲)
 更多
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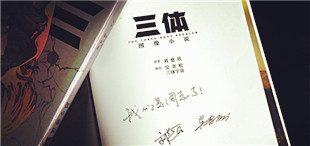
吴青松:我把画《三体》当成是一场修炼
“我把画《三体》当成是一场修炼,修炼可以为之后的创作提升能力,同时在其间隙,也能为之后的创作做好更充分的准备。”
 更多
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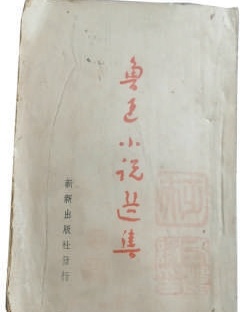
石舒清:三本书的收藏记忆
记得大概十年前,我买到一本版本很是特别的《忠王李秀成自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