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epseek之后,创意写作走向何方?

4月1日,科幻作家陈楸帆做客“新媒体创意写作”课堂,为同学们带来一场题为“Deepseek之后,创意写作走向何方?”的讲座,讲座由课程负责人樊迎春主持。
樊迎春老师在开场介绍中指出,陈楸帆是一位兼具传统与先锋特质的作家。他的传统性体现在其科幻作品始终贯穿着现实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关怀;先锋性则表现在他勇于探索、敢于解构,近年来更是积极尝试人机互动写作,不断以创作实践做出对现代性的反思。“新媒体创意写作”课程邀请他作为嘉宾是题中之义,相信他能为同学们提供关于新媒体时代科幻文学创作、改编与人工智能等问题的别样经验与独特视角。
课堂开始后,马海晴和诸俊飞两位同学分别以《一黛不如一黛?——从林黛玉的形象变迁看经典IP的改编困境》和《后人类主义视角下的AI与写作》为题做了报告,前者从不同版本的《红楼梦》影视剧中林黛玉这一经典却难以演绎的形象切入,探讨了经典IP不断被改编的原因与困境;后者则从名为韩国作家创作,实为Deepseek产生幻觉、自己生成的科幻小说展开思考,在后人类主义的视域下探讨了AI写作的现状、限度与可能。
陈楸帆对两位同学的报告进行了点评。他认为,马海晴提出的“一黛不如一黛”揭示了媒介革命如何改变了我们的认知、导致经典文本的多义性流失及审美体系的变迁乃至崩坏这一重要问题。我们是否还能回到所谓“经典版本”的《红楼梦》?又该如何让文本呈现出新的可能?这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针对诸俊飞的报告,陈楸帆分析了AI训练数据的偏差性,并延伸至后人类主体性讨论,强调人机交互已打破传统认知边界,形成无法清晰界定的混合主体性。也正是在这种混杂语境中,人文学科的重要性得到凸显。
由此,陈楸帆开始了他对于人工智能与创意写作思考的分享。他指出,从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开始,人类就一直“热衷于创造怪物”,而“怪物”对自身身份的质疑——“我是谁?为何被创造?”——则从科幻文学的诞生之初就不断以各种变奏形式出现,当下的AI,某种程度上也扮演着这个“怪物”和“他者”的角色。
随后,他援引Amara定律分析技术发展的非线性特质:“我们总是高估技术的短期效益,却低估其长期影响。”以互联网为例,它曾被寄予构建平等信息社会的厚望,但最终却陷入算法垄断与信息茧房的悖论。AI的发展同样如此:从1956年达特茅斯会议提出“人工智能”概念,到人工神经网络在90年代的边缘化挣扎,再到Transformer架构引发的生成式AI革命,技术的进化始终以螺旋式对抗的方式进行。
作为一位长期关注AI的科幻作家,陈楸帆也分享了自己与AI合作的创作经验。早在2019年,他就在《人生算法》一书中尝试与AI合作创作。他与好友将他的作品作为训练数据,开发了一个小型模型,即“陈楸帆2.0”,可以用他的文风生成新内容。然而模型生成的内容支离破碎,他被迫为这些“无意义的胡言乱语”创造上下文。不过陈楸帆指出,人类把模型讲的故事圆上这种“意义赋予”的过程,恰恰也是文学的核心功能。同样在2019年,《思南文学选刊》创新性地使用AI评委为上一年的所有小说打分,陈楸帆利用AI辅助创作的小说《出神状态》以0.00001分的微弱优势胜过莫言的《等待摩西》。这个“斯普特尼克时刻”让他意识到,“现实已经超越了科幻的想象,开始挑战人类虚构的界限”。
面对AI带来的冲击,陈楸帆提出了积极应对的策略。他认为,这是“有史以来,人类第一次拥有与一个异构大脑(机器智能)相互激发创作灵感的机会”。我们应该思考如何在人机时代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积极理解并利用AI技术激发创作灵感,比如用项目经理的思路为每个模型分配最适合的工作,搭建AI流水线。只有逐步建立起对新技术的认知缓冲带,才能适应快速发展的科技周期,步入人机协同的未来。不过,陈楸帆也提醒大家要审慎地对待AI,不能被它们所驱使和压倒。他主张“把AI作为方法,作为观照人类界面的界面”,以此为契机来更好地理解何为写作、何为文学乃至何为人类。与其追问“AI是否有创造力”,不如思考“人能否在机器的帮助下更有创造力”。
陈楸帆还从“AI参与创作的作品能否获得人类奖项”以及“如何界定AIGC的知识产权、权利归属及利益分配”两个问题切入,剖析了当前人类在使用AI方面存在的问题。在他看来,有关AI的一切讨论最终都要回归到一个根本问题:人是什么?人在世界中的位置在哪里?而文学作为理解人类的界面之一,不仅是对外部世界的映射,更是对内部世界的转译,恰好能在此时提供帮助。因此,他提出了“深度写作”(deep writing)的概念,将写作视为通向人的意识深处、改变人对外界认知、重新寻找生命意义与价值的实践。
最后,陈楸帆以生态学隐喻总结技术与人类的关系。他反对启蒙运动以来的二元对立思维,主张人类与机器处于共生进化网络中,正如蜂鸟与花朵相互依存,人类与AI也在塑造彼此的未来。“一切都在变动之中互相形成,只有接受这种变化,我们才能与机器也好、与其他物种也好、与整个生态系统也好,一起超越怕与爱,去形塑新的未来、新的现实。”
讲座结束后,樊迎春老师进行了回应。她认为,在内容与形式都处于巨变的时代,陈楸帆的讲座再一次提醒我们媒介即隐喻、媒介即认识论。AI既是解构又是创造的工具,它作为人类智慧的产物,为我们提供了重新认识自我边界的机会,也再不断催促我们厘清和发掘“人”的不可替代性。如果人类可以与AI共生共创,共同探索更广阔的创作可能性,把AI作为方法,作为观照人类界面的界面,这种相互激发的状态也许是最具普适性、最解构也最建构、最高级的人文主义。随后,同学们就为何选择创作科幻小说,创作时如何搜集整理信息等问题向陈楸帆提问。陈楸帆强调要始终保持对前沿领域的好奇心,而科幻可以容纳很多互相矛盾的存在,充满了可能性。在他看来,很多时候“科幻不是在预测未来,而是在创造未来”。(摄影:陈晓彤)
 更多
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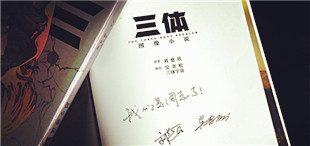
吴青松:我把画《三体》当成是一场修炼
“我把画《三体》当成是一场修炼,修炼可以为之后的创作提升能力,同时在其间隙,也能为之后的创作做好更充分的准备。”
 更多
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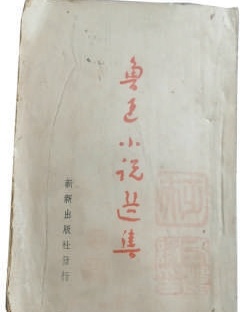
石舒清:三本书的收藏记忆
记得大概十年前,我买到一本版本很是特别的《忠王李秀成自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