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培源:穿越经验的边界
家乡澄海是著名侨乡。与之相关的“词和物”(“红头船”“过番”“下南洋”“暹罗”等)经长辈口口相传注入我的记忆,有意无意间加深了我对潮汕的认同(但也仅此而已)。我长大的小镇叫盐鸿,邻镇东里有樟林古港,多年前被开发成景点,河道中矗立一艘巨型的仿古红头船,仰头睇,有巍峨状。从前海运鼎盛时,港口边新兴街的栈房货如轮转。有一年,我与友人在那一带游逛,港口繁华已成过往,只见破厝几落,长满荒草,形同废墟。后经修葺,新兴街和古港才有了如今的光鲜模样。
我在《金缕衣》里写过水仙寺——一处离樟林古港不远的寺庙,不过仅是将它当成人物活动的背景之一,从未想过,有天会把从此处坐红头船“过番”的华侨写进小说,以虚构的形式触碰家乡这段被咀嚼了无数遍的历史。据记载,有清一代,雍正至咸丰年间的一百多年里,自樟林港下南洋、过暹罗的潮汕人多达百余万。《重游》里第一代过番的父亲,从这里出海,辗转香港,最终落脚于马来西亚。这是小说创作的“前史”。
《重游》讲的是一位华侨一家三代的故事。如果依循传统写法,或可调用第三人称,沿时代的脉络,写成一部略带“史诗”意味(哪怕装模作样)的“大中篇”,少则三五万,多则七八万字。但我对此有所警惕,构思时想的是另辟新径,从当下切入,以人物之口现身说法。由是有了开头筵席一幕:“我”应邀返乡参加电影节活动,邂逅来自马来西亚的老华侨。席上众人听他讲当年其父从潮州下南洋到槟榔屿讨生活的故事,以及他此次返乡的目的。这部分用的是转述,兼顾讲话人(老华侨)的第一人称口吻。“说者”与“听者”同时在场,由是时空可腾挪并置,不再拘泥于线性的条条框框,篇幅自然裁短。几经删改,完稿时不过两万字出头。
回想起来,最难写的也是这一部分。我从来没有去过马来西亚,怎么挣脱边界,把陌生的经验化进小说呢?没有捷径,只有硬着头皮,亦步亦趋。小说牵涉的部分事实要核查——大到历史节点和事件,小至人物的爱好和生活空间,必须在想象与现实的钢丝上踩稳脚步,才能走完这趟虚构之旅。
好在反复折腾,总算写成。从去年七月写到十月,教学、带娃之余,一有空就沉进故事里。这一过程,仿佛打开了一条坦途,让我得以穿越自身经验的边界,探入未曾抵达的领域,去和历史以及那些被时间洪流冲刷和裹挟的人会面,听他们说,也让他们听我说。更有趣的是,我把曾经生活过一年的香港也“嫁接”进来了:昂坪的缆车、天坛大佛、铜锣湾鹅颈桥下“打小人”,记忆复活,闪闪发光,与《重游》里那对父子的足迹叠合呼应。
感谢首刊《重游》的《芙蓉》杂志,感谢《中篇小说选刊》编辑青眼!
 更多
更多
苏童:我认为生存比死亡值得书写
“读者感受到的是文字融合在一起以后的气息,它超越了一切感官,它本身是有力量的。而技术结构本身没有力量的,它可以很完美、很科学,但是它不产生任何力量。”
 更多
更多

随笔杂谈 | 从山肌到鹅卵石
我,本是大山的一块肌肉。在岁月的长河里,曾长久地傲立在那高高的山巅之上,与蓝天白云为伴,与清风明月为友。

散文 | 藜杖青衫叩古秋
本文围绕“青衫客秦淮云梦”在“杖藜行歌”过程中的双重体验展开——对“旷达”生命境界的深刻领悟(前半部哲思升华)与深秋时节刻骨铭心的“孤寂”感(后半部情感宣泄)。通过多种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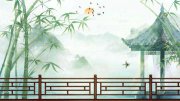
随笔杂谈 | 闲说小满
立夏刚脱胎于春,或许尚留有春的余韵,小满不同,那眉眼、那浑身的气派,谁能说不是夏的嫡传!

诗歌 | 渡(组章)
把自己留在最后,又随哪阵风流浪,风会把自己带走吗?自己永远不是自己。

散文 | 瓦屋山“寻幽”
寻觅一处清凉之地,安放自己躁动的身心,于是,义无反顾投奔四川洪雅的瓦屋山,投奔瓦屋山大峡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