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烟》:乡土叙事中的经济学与社会学视野
杜万青的长篇小说《青烟》表面上看是一部非常“传统”的作品。
一个名为四岘四水的乡村世界、几个大姓人家的勾心斗角、一个家族的由盛转衰、若干或是坚守或是堕落的人物形象……这些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至少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定型,类似陈忠实《白鹿原》这样典型的乡村叙事。
这似乎也颇为符合作者本人的定位。杜万青出生于1955年,20世纪80年代怀揣热情登上文坛,之后辗转于教育、商业,阔别文学数十年。种花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一出手,还是当年的味道。
然而这只是表象,细读就会发现,《青烟》在种种“旧”的东西中裹藏着很有意义的新质。
作品着重刻画了乡绅阶层与民间资本在20世纪上半叶的“脆弱性”和“依附性”。这种经济学与社会学视野,能给经典的乡土、传奇、劳动叙事带来新的启发。
先说《青烟》对乡绅阶层和民间资本“脆弱性”的呈现。
故事开始于清末,主线是四岘四水首富薛五佬家的“败家史”。其衰败有两个关键节点,其一是薛五佬死后,独子薛驹在赌场一掷千金,其二是国民党县党办督查专员以抗日之名要薛家出一万大洋(实为专员借机贪污)。
作者对第二个节点的描写堪称精彩。
专员只用一个班的兵力,枪毙两条狗、杖责一个德高望重的老人、软禁一个大户,就在谈笑间刮走大户们的几大箱银元。所谓“巧取豪夺”究竟如何实现?这种带有“厚黑”性质的场景在大多数作品中要么写得过于传奇化,要么一笔带过,《青烟》难得将专员表面客套实则步步紧逼的话术、手段和大户们的反应写得非常细致、真实。
第一个节点则很容易被忽略。
“败家子赌博”是乡村叙事中容易吸引读者共鸣的经典桥段,然而读者在道德层面的愤怒、批判很有可能掩盖这一桥段背后的“经济学问题”。像《青烟》中薛驹这种坐拥千亩土地、上万银元、成群牲口、深宅大院的大户独子,真的能因为个人的赌博而败家吗?他用一袋袋银元、地契去“打水漂”,仅仅就是因为赌场的圈套和自己的愚蠢吗?
闲家一直输的赌局,人们往往认为是赌场出老千所致。民间故事和香港电影给人留下一个牢不可破的印象,即千术在赌场上是万能的,只要有千术就可以在赌客手中“空手套白狼”。
但实际情况可能远没有这么简单,能短时间将薛家这么大的家业敲诈干净,小小赌场背后必然涉及数倍甚至数十倍于薛家钱财的资本运转——也就是说,《青烟》对“败家子赌博”这一经典桥段的详尽刻画,背后有值得探索的空间。
赌场章节一开始就交代了小小的土门子赌场背后是马步芳——赌场给薛驹设套,使其荡尽家财,其实质是军阀势力凭借武力对乡绅阶层敲诈勒索。
这也相当符合近代史的实际情况。看似娱乐场所的大小赌场背后往往盘踞着军阀或地方势力,富人与穷人的钱无分彼此,不舍昼夜地流过这个黑暗的孔洞,化作徘徊于权贵之间的政治资金,也变作硝烟战火中的火枪大炮。
进而《青烟》这部作品看似写得与世无争,四岘四水仿佛“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其实书中人的一举一动,无不是大历史的组成部分。
于是书中那些看起来相当常规的乡村世情、辛勤劳动就呈现出了另一种意味:乡绅们在战乱中惴惴不安,他们曾经引以为豪的家产正在变成最危险的东西;而还未跻身于此的农民白天熬肠刮肚,用血汗滋润土地,夜里幻想着成为前者,浑不知危险为何物。
小说最出彩的人物形象之一是农民韦黔,他就是后者中的一员。
韦黔有十个儿子,是名副其实的“大户”,但他没有薛家那么大的家业和崇高的地位。他“卧薪尝胆”,像狩猎的蜘蛛般等待薛家的衰败。直到赌场拍卖薛家的田产,韦黔带着早已佘借好的现洋登场,通过“拾跌果”的方式一跃成为有薛家田产最多的人,住进昔日属于薛五佬的深宅大院。
韦黔喜得痰迷心窍差点暴毙,但很快就发现自己的美梦并未实现。
过去薛五佬是靠给凉州驻军提供军粮,才有了和县太爷把酒言欢的资本。现在韦黔恨不得把自己拍卖来的房产地契都贴到脑门上,也只能在村民的婚宴上坐在院子里。
登堂入室、坐上炕桌的是谁呢?是田产远不如韦黔,但却有个“保长”儿子的蒲正席。
为了获得尊重、维持家业,韦黔进一步勒紧全家人的裤腰,裁剪长工的伙食,却也只得到了一个近似“周扒皮”的名号。一生要强自诩聪明的韦黔到最后也没有想明白一个道理——对于当权者的“依附性”,才是当时乡绅阶层与民间资本生存的本质。
如上只谈到《青烟》诸多面相之一。这是一部复杂的作品,同时也是一部容易被“误读”的作品。
它的开篇阶段就不可避免地让人联想《白鹿原》《活着》甚至《霸王别姬》这些经典的文学与影视作品,进而让自身显得平凡;而只有穿越这些障碍,我们才能看到《青烟》作为乡村叙事内部的新质,看到其在经济学与社会学角度的新写法对相关创作的启示。
(作者为中国作协创研部副研究员,辽宁作协特聘签约作家)
 更多
更多
苏童:我认为生存比死亡值得书写
“读者感受到的是文字融合在一起以后的气息,它超越了一切感官,它本身是有力量的。而技术结构本身没有力量的,它可以很完美、很科学,但是它不产生任何力量。”
 更多
更多

随笔杂谈 | 从山肌到鹅卵石
我,本是大山的一块肌肉。在岁月的长河里,曾长久地傲立在那高高的山巅之上,与蓝天白云为伴,与清风明月为友。

散文 | 藜杖青衫叩古秋
本文围绕“青衫客秦淮云梦”在“杖藜行歌”过程中的双重体验展开——对“旷达”生命境界的深刻领悟(前半部哲思升华)与深秋时节刻骨铭心的“孤寂”感(后半部情感宣泄)。通过多种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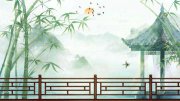
随笔杂谈 | 闲说小满
立夏刚脱胎于春,或许尚留有春的余韵,小满不同,那眉眼、那浑身的气派,谁能说不是夏的嫡传!

诗歌 | 渡(组章)
把自己留在最后,又随哪阵风流浪,风会把自己带走吗?自己永远不是自己。

散文 | 瓦屋山“寻幽”
寻觅一处清凉之地,安放自己躁动的身心,于是,义无反顾投奔四川洪雅的瓦屋山,投奔瓦屋山大峡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