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藤:少年记忆的发酵
故乡北山有个柞蚕场,坐落在一条人迹罕至的山沟里。生产队时期,蚕场干活的都是些青壮年,因为离村有几十里路程,往返不便,男男女女就住在蚕场的窝棚里。我上小学时有个姓车的民办老师在蚕场干过给柞树截头的活儿,得空儿就给我讲些蚕场的见闻,故事的主角有人,有狼,有狍子,最多的还是蚕。车老师讲故事绘声绘色,妙趣横生,把蚕种在了我心里。
车老师讲过两个事让我记忆犹新,一个是蚕能预测寒冬还是暖冬。如果蚕在秋后做的茧很薄,这个冬天一定不冷,是暖冬;如果蚕茧很厚,则必然是寒冬,人们需做好御寒准备。另一个是蚕蛹懂人言。车老师言之凿凿,没有胡诌八扯的迹象。出于好奇我还真试过几回。将蚕蛹头朝下立在盛了米的碗里,然后我贴近它说,摇摇尾巴。蚕蛹果真就会摆动几下,说朝东摇,它就会朝东偏一下,说朝西摇,它也会照做。现在想起来我还觉得神奇,没有五官的蚕蛹靠什么能听见人说话?难道真有一种看不见的丝与人相连?
前些日子,我萌生出写一写少年经历的想法,自然就想到了蚕,想起了车老师当年讲的故事。我觉得蚕确实值得写一写,蚕的一生是为了使命而来的一生,造字的先人显然知道这个道理。因为把蚕字拆开来看,就是天虫,这两个字隐含着蚕是上天赐给人类来解决穿衣问题的神虫。而伏羲化蚕、嫘祖始蚕,都给蚕涂上了层层神秘的色彩。蚕对于中华文化的形成和传播可谓功莫大焉,没有蚕,哪里会有后来的丝绸之路?
这几年,我对草木、动物、昆虫产生了浓厚兴趣,写了许多此类题材的长中短篇小说,越写越觉得万物可爱,越写越觉得它们值得写。我写了鹰、驴、狗、猫、猞猁、貔子等十几种动物,写了蟋蟀、螳螂、蝈蝈、蜣螂、甲虫、蜻蜓等十几种昆虫,写了中国北方三十几种花草树木,写它们的过程也是受它们影响的过程。比如说树也会发脾气,猫颇具君子之风,驴遇倒卧之人则止步,看似蠢笨的猪会跪地向主人求饶,等等。由这些发现,我理解了庄子为什么要写《齐物论》,理解了孔子对弟子读《诗》的要求。其实,孔子的要求不仅是多识鸟兽草木之名,重点是对自然、对万物的认知和敬畏,他本人因“西狩获麟”而垂泪的故事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在《天虫》中我写了一个厨子和一个养蚕女若隐若现的爱情历程。他们两人的爱情并不轰轰烈烈,也毫无浪漫可言,会吹笛子的田娥就像一只不断蜕变的蚕,虽命运悲催,但始终有尊严地活着,不要怜悯,不求救赎,她最终有了属于自己的归宿。小人物的爱情也是爱情,甚至比许多带有附加条件的爱情更纯洁,更有温度。
 更多
更多
苏童:我认为生存比死亡值得书写
“读者感受到的是文字融合在一起以后的气息,它超越了一切感官,它本身是有力量的。而技术结构本身没有力量的,它可以很完美、很科学,但是它不产生任何力量。”
 更多
更多

沈从文与王澍:始于1980年代的跨界对话
1987年,王澍沿着湘西沅水,完成了为期三个月的旅行。
 更多
更多

随笔杂谈 | 从山肌到鹅卵石
我,本是大山的一块肌肉。在岁月的长河里,曾长久地傲立在那高高的山巅之上,与蓝天白云为伴,与清风明月为友。

散文 | 藜杖青衫叩古秋
本文围绕“青衫客秦淮云梦”在“杖藜行歌”过程中的双重体验展开——对“旷达”生命境界的深刻领悟(前半部哲思升华)与深秋时节刻骨铭心的“孤寂”感(后半部情感宣泄)。通过多种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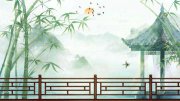
随笔杂谈 | 闲说小满
立夏刚脱胎于春,或许尚留有春的余韵,小满不同,那眉眼、那浑身的气派,谁能说不是夏的嫡传!

诗歌 | 渡(组章)
把自己留在最后,又随哪阵风流浪,风会把自己带走吗?自己永远不是自己。

散文 | 瓦屋山“寻幽”
寻觅一处清凉之地,安放自己躁动的身心,于是,义无反顾投奔四川洪雅的瓦屋山,投奔瓦屋山大峡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