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之先生,《文史知识》一直珍存着
读了2024年11月8日《中华读书报》杨牧之先生的文章《臧老看过的杂志,还保存着吗?》,欣喜之中,我真可说是感慨系之。牧之先生是我父亲臧克家的老朋友,是我们非常尊重的一位长者,那些逝去岁月中的往事,给我们留下了不少难忘的记忆。文章中,他用饱蘸情感的笔,回忆了与我父亲的多年交往,尤其是对他主编的《文史知识》杂志的喜爱、关注和支持。文中满满的细节描写,将我父亲的性格为人刻画得真实而生动,其中一些有趣的情节,让我在忍俊不禁会心一笑的同时,心头涌上许多难忘的往事和鲜活的场景。
虽然时光已经过去数十年,但我至今清晰地记得父亲对《文史知识》的偏爱。他在写于1989年7月11日的散文《第一号朋友——贺〈文史知识〉出刊百期》里,绘声绘色地写活了当时的情景:“我每月收到几十份刊物,但认真阅读的只有《文史知识》与《古典文学知识》。特别是前者,从它诞生那天起就与我结下了不解之缘。我每期必读,几乎从头到尾,不放过一篇;每篇,不放过一个字,红铅笔划的红条条,钢笔划的蓝道道,满纸皆是。甚得我心的字句上,加了圈,有的加了双圈。作为提要,在纸边标出重点,再查阅时,一目了然。个别不易发现的错字,我在旁边打个‘×’。我这样自许:在全国读者群中,我算是《文史知识》的第一号朋友了。”“白天,事多分神;夜读,最为称心美好了。我习惯8点多钟上床,体舒神怡,打开《文史知识》,如良朋对晤。冬天,炉火微温,灯光柔媚,思接千载,神游文海,读到会心之处,灯花也为之灿然,炉中爆炸声作,似与我心共鸣。不觉10点已过,于是掩卷,而安然入睡。”
说起来,父亲真不愧是《文史知识》的“第一号朋友”。他不仅仔细阅读、批注这本杂志,对于偶尔看出的个别错字和错的标点符号等问题,都会马上告知牧之先生以求更正,并对杂志提出过中肯的意见和建议;喜逢杂志创刊5周年和出刊百期,老人立即写去贺诗贺文,以示衷心的祝贺……除此之外,从1982年第一期开始,直到85岁时的1990年第六期为止,他先后为杂志撰写了近十篇文章:《重读〈岳阳楼记〉》(1982年)、《真相与真魂》(1985年)、《贺〈文史知识〉创刊5周年》(1985年)、《姜白石的〈齐天乐〉》(1985年)、《悲惨阴暗的战争画卷——重读〈吊古战场文〉》(1986年)、《名句别解——宴小山〈鹧鸪天〉“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1988年)、《悲歌一曲了此生——徐君宝妻〈满庭芳〉词读后》(1989年)、《第一号朋友——贺〈文史知识〉出刊百期》(1989年)、《一字之差 境界全非——重读杜牧的〈秋夕〉》(1990年)……这些文章不仅表现了父亲在古典文学赏析领域的深厚功力,更是他发自内心的对于杂志的鼎力支持。他这位“第一号朋友”名副其实!
父亲当年阅读这本杂志的时候,已是在文坛耕耘了半个世纪的古稀老人,文史方面的知识并不匮乏,虽然这阅读里有喜爱,有乐趣,但他夜半捧读、坚持不懈的动力到底是什么? 他多次对我们提起这个话题。父亲说,即使是某个领域的专家甚而是大家,也不可能对所有知识掌握得面面俱到,因此就应该不计年龄、不畏困难地多多学习、涉猎各方面的学问。他还说:“因为年老了,大家高看我;其实,腹内空乏,大叫好,令我大惭;小叫好,令我小惭。为了减少惭愧之情,只有努力学习,以充实自己,决不能不知以为知,欺人以自欺。”他就是以自己诗中所写的“余年不计去时多”的“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来阅读他所喜爱的《文史知识》,来苦读堆放在床头的艰涩难啃的古典文艺理论书籍的。父亲讲到他从这本杂志中获取了不少以前未曾掌握的知识,还叮嘱我们多读读这本杂志,以此充实自己,开扩眼界。
牧之先生在文章里曾讲到这样的往事:在每天骑车上下班的路上,常遇到出门散步的我父亲。于是,老人“总是笑着冲我走过来,站在我的自行车前,把着自行车车把,和我说话。什么都聊,天气,他这两天又写了什么,昨晚新闻联播里有趣的新闻……当然聊得最多的是我当时主持编的《文史知识》,哪篇文章好,哪篇文章他认为有问题。我真是得天独厚,经常能得到这样一位大家的指导。”但是,“有的时候,我上班有急事要办,没时间停下来聊天。后来,我有时就拐个弯,不从他家门前经过。过两天,见到我他准问,这两天出差了吗? 我很不好意思,不敢说谎,只好笑笑。”读到这里,我眼前立即鲜活生动如昨日般地浮现起多少情与景呀!
父亲是一位非常有毅力且生活规律的人,一天四次到我们住了四十年的赵堂子胡同散步,是雷打不动的锻炼身体的好方法。一年四季,酷暑严冬,风中雪里,从不间断。那时,老人沿着路边漫步的身影,成了胡同中独特的风景。在这里,发生过许多感人的故事,被多少人写进了优美的文章,刻入了自己的记忆。我曾在2004年7月父亲去世后写成的散文《短巷情长》中,这样描绘道:“每当父亲漫步在赵堂子胡同中,你看吧,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骑车的,步行的,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身份和阶层的人们,都纷纷亲热地向他招呼问好,有的还要站在路边聊上一会儿。那些孩子们更是可爱,每逢中午和傍晚放学的时候,由稚嫩的、羞涩的、粗放的孩子们的嗓音,此起彼伏地交汇成的‘臧爷爷好’的问候声不绝于耳。有时,整个路队的小学生,由前头打着小旗的路队长带领,齐声向老人致意。从幼儿园大门走出的小不点儿,会抱着我父亲的腿撒上会儿娇。……每当我目睹这感人的画面,每当我在院中的屋里,都清晰地听到大门外传来的阵阵问候声,我便会在深深的感动和震撼之中,情不自禁地发出感慨:人活一世,得到人民群众如此的爱戴,我亲爱的父亲真是此生足矣!”我深深知道,父亲得到了人们如此的尊敬和热爱,是因为他为大家付出了很多很多……牧之先生就是身入其境的亲历者,数十年后,他还被我父亲那待人热情如火的赤诚之心感染着。老人与牧之先生、《文史知识》的这段往事,被我们记在了心间。而牧之先生因有紧急公务要办,故上班时骑车绕路而行的过往,则成为足见我父亲真性情的有意思的憾事。此刻,让我含着会心的笑向先生致以迟到的歉意吧。
牧之先生的文章,不同寻常地用了一句问话当作题目:《臧老看过的杂志,还保存着吗?》,令我读来非常亲切,并且有一种立即作答的冲动。我特意把这篇文章推荐给保管着父亲遗物的妹妹,她为此专门去查看了老人留下的刊物。现在,我们可以郑重而自豪地回答:请牧之先生放心,父亲读过的《文史知识》,我们一直小心地珍存至今,一本也没有丢失和损坏! 先生在文章中还有这样一段话:“记得当年臧老给我翻看他在《文史知识》上的批注时,我几次想要把他批注过的这本杂志讨要下来,但终没好意思开口。后来,很是后悔!”时光过去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已逝父亲的这些批注本更为珍贵。身为子女的我们,很愿意代表早已驾鹤西去的老人,精心挑选一本似有余温的《文史知识》批注本,带着对往昔不灭的记忆和眷恋,将它邮寄到牧之先生手边,来弥补那看似已无法弥补的遗憾。我想,天堂中的父亲看到这两篇有问有答相互呼应的文章,看到故去二十多年后,老朋友和孩子们对他依然不变的深深忆念,看到我们替他实现了当年牧之先生始终没好意思开口的心愿,一定会赞许而欣慰地点头微笑吧?
 更多
更多

肖复兴:读书,是一辈子的事情
“第一本书的作用竟然这样大,像是一艘船,载我不知不觉并且无可抗拒地驶向自己意想不到的地方。”
 更多
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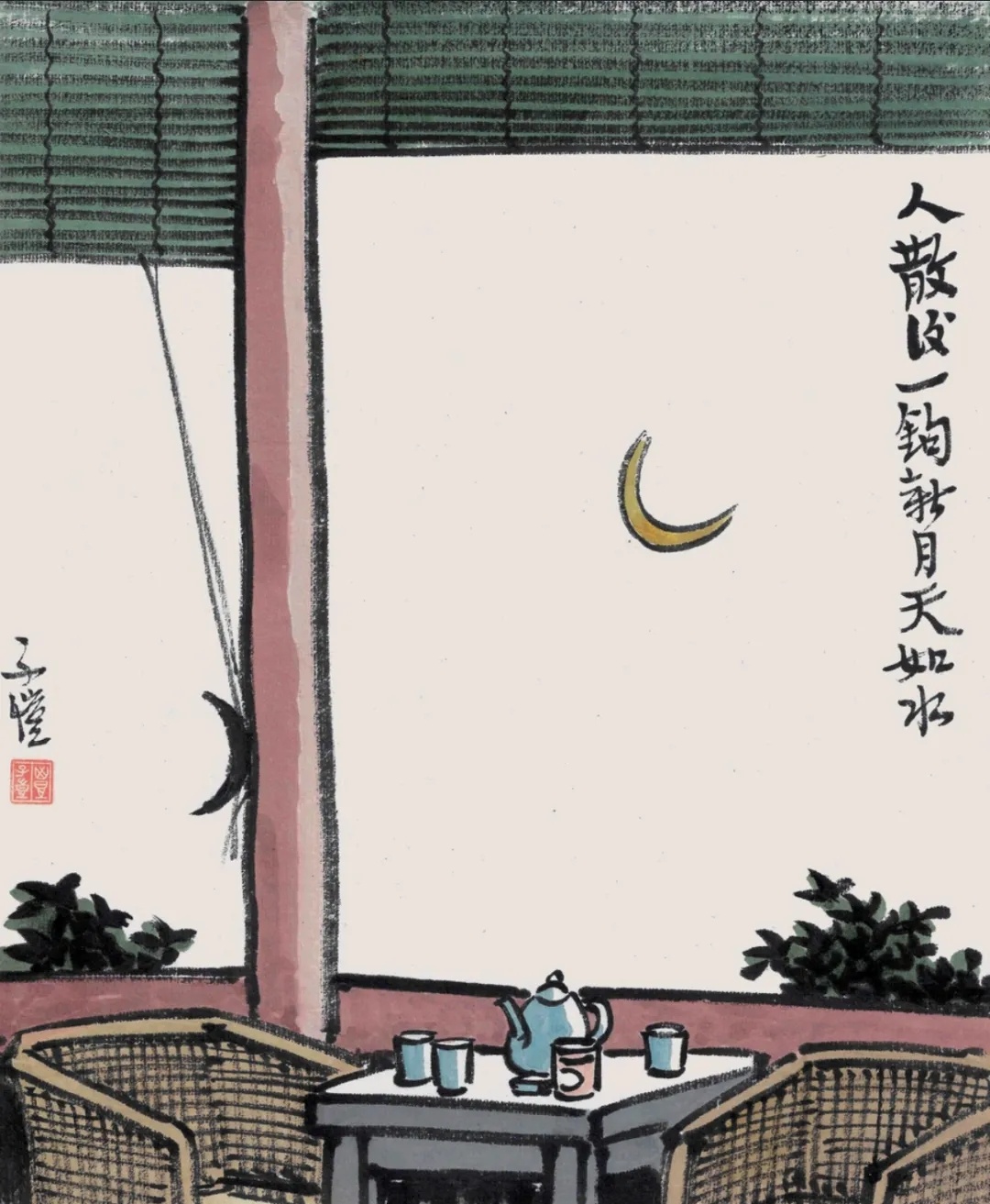
王军: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
“人的一生,遇上过多少个一钩新月天如水的夜?”
 更多
更多

散文 | 母亲的老布鞋
以“母亲的老布鞋”为线索,串联起母亲大半生的辛劳与温情,制作老布鞋的细节与爱意,以及象征意义。

散文 | 松魄千霜
本文以青衫客从初见的惊叹,到触摸时的感佩,到听涛时的共鸣与自省,再到对画松、听心、持守等问题的思考与回答,最后以充满敬意的告别作结,形成一个完整的欣赏与感悟历程。赋予松树

散文 | 爷爷
对爷爷的怀念

散文 | 公竟渡河
大禹劈山,北魏凿石,登天梯跃龙门,不是同一批人,却是同样的人。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倔强,那种九死无悔绝不丢盔弃甲的刚韧,那种不计成败敢在绝路中走出生路的孤勇,用河津话

诗歌 | 年轮之上(组诗)
中年之后,终于慢下来了 管理的园囿,越来越少 时间的绳索,一点点勒进躯体 生活的卷帙,著述颇丰 他们喟叹一声,年轮的指针 晃了晃,像不息的小小寰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