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作为对世界苦难的质询 ——托芙·迪特莱弗森长篇小说《面孔》
在迈克尔·坎宁安的长篇小说《时时刻刻》(The Hours)中,坎宁安设置了处于三种时间线索中的三位不同女性,其中对于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刻画生动而深刻。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其中关于“两个世界”的一段剧情。那日,伍尔夫的妹妹来到她的家里,此前伍尔夫因为要准备接待客人而陷入慌乱,此时她正受到精神症状的折磨,几乎无法驾驭诸如让佣人做什么饭菜这样的小事。妹妹和她的三个孩子的到来让伍尔夫很开心,但同时她有无数次滑入到情绪的漩涡当中无法自拔的风险相伴。她依然沉浸在如何构思自己的小说《达洛维夫人》的困惑与焦灼中……在与妹妹交谈的时候,她想到如何处理她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的命运,因此她陷入到全然忘我而失神的状态里,以至于根本没有听见眼前她妹妹跟她说的话。这招来了两个男孩的嘲笑,她们显然认为他们的姨母异于常人,感觉到异常和滑稽。此时,她妹妹对两个孩子说,你姨母跟我们不同,她生活在两个世界,而我们只生活在一个世界。这一场景刺痛了我,其中的滋味难以明了,这是一种极大的对冲,关于一个以精神生活为生的人如何能够同时理智地生活在两个相互撕扯的平行世界,并面对现实生活对于精神生活那古老的敌意。
也许,你会说,这算什么问题?!但是,一旦你认识到了这是一个多么重大甚至古老的母题,你才会明白那种强烈的分裂感和无力感的来源。“两个世界”对于一些人来说的的确确是一种精神境况和灵魂处境。当“两个世界”尚且可以和睦相处时,一切都还不算太糟;但当有一天这“两个世界”已经无法分出边界,变为一滩浑水,继而分不清哪一个是现实,哪一个是想象世界之时,处于现实世界当中的人无可避免地陷入癫狂与分裂,这将是怎样的一个艰难时刻呢?
丹麦小说家、诗人托芙·迪特莱弗森的长篇小说《面孔》正是聚焦于这一时刻。托芙·迪特莱弗森是20世纪丹麦国宝级作家,她生于丹麦的哥本哈根,在那里她度过了灰暗的童年。她少年成名,婚姻之路却屡遭坎坷,经历四段婚姻并深受酗酒和药物成瘾的困扰,多次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小说《面孔》聚焦于一位备受赞誉的作家莉塞·蒙杜斯在精神病院前后的一段故事。此时,这位女作家陷入写作危机,两年没有新作品的她身心处于极度焦灼的状态,而与此同时,她的丈夫格特和女佣人吉特之间又出现了婚外情感,三个儿女与作家的关系也出现了问题。在这样的巨大压力下,莉塞出现了幻觉,她坚信丈夫和情人正在密谋杀害自己,一时之间各种恐惧猜疑构成了一堵她无法穿越的墙,与周围人的疏离让莉塞愈加陷入疯狂,幻视幻听随即出现,真实和虚幻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最终,莉塞因为失去理智而胡乱吞服了过量的安眠药被判定为有自杀倾向而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在精神病院治疗期间,莉塞的整个世界都处于一种分裂与混沌的状态中,无论是医生、护士、病友,还是现实生活中的丈夫、孩子、母亲这些面孔接二连三地以错乱的方式出现,面孔生发出原本没有的形态,说话方式,以及情节,进行着错误的安置,并不受控制随机出现,有时在病房的格栅后面,有时从枕头里升出来……这让莉塞应接不暇,因此产生的错置也让她更加受到疯狂的入侵。她的脑中世界就像是一个纷乱的幻影之城,而她已经无法分辨究竟何为真实何为虚构了……
脱序:作为挣脱社会对应物的面孔
小说的重点落在对于面孔的描绘上,面孔不仅仅代表着现实世界当中对莉塞构成威胁与压力的人,也代表着在分裂出来的幻想世界中屡次出现的幽灵般的存在。小说开端就指出:“她一直避免上街,因为成群的面孔令她害怕。她不敢接受任何新面孔,又害怕在此遇见那些老面孔。”而在精神病医院治疗期间,“格栅”作为一个莉塞与外部世界之间隔绝的象征性存在,屡次出现在她的幻觉世界。每当这个时候,总有面孔出现在这里,这些面孔有时候是吉特,有时候是格特,这些面孔带着现实生活中他们的身份,有时带有着对于莉塞所不能完全认知的目的和语言。“高处格栅”里有时还会有凶残的酷刑,这是莉塞内心当中最残酷的经验的象征。面孔的错位不但显示了莉塞混乱的现实与幻想世界。面孔作为象征物代表着一种秩序,面孔的移位代表着秩序的混乱,而面孔回归到自身原有位置则代表着秩序的回归。这既是现实中每个人的位置和秩序,同时也是莉塞内心理性的秩序。
面孔作为莉塞疯狂的表征,彰显了她疯狂的源头。疯癫作为这本小说的核心拥有了全新的意义。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中,女性主义批评家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利用女性主义的视角归纳了19世纪文学中的“疯女人”形象。“当简·爱与罗切斯特跨越身份地位的差异,终于要宣誓结合时,一个疯女人的出现粉碎了简·爱的一切梦想。”“疯女人”作为一个秩序的破坏者,作为一个人们身体里蕴藏的企图打破一切秩序的象征形象,正是现实当中女性长期被压抑的那个非理性自我的镜像。莉塞们正是在生活和地位被全面压抑,在爱欲当中无法全然满足的长期折磨当中一步步变得疯狂的。而在《面孔》当中,我们说,“疯女人”这一19世纪以来的典型文学形象已经从“阁楼”走了下来,她步履蹒跚,宛如杜尚画中《下楼梯的裸女》,在日渐分崩离析中成为一个诸如莉塞一样的普通的家庭主妇,同时慢慢走向疯狂的边缘。如果小说中,莉塞对于丈夫众多情人表现出的默许被视为卑微之举的话,我更愿意将莉塞的无动于衷甚至麻木看作一种她对于打破男性崇拜的有意识的冷漠化,即她以此种方式来反抗甚至告别她作为妻子的身份规约,而长期以来,对于性权利的占有是夫妻关系的唯一表征。正如法国女性主义者埃莱娜·西苏所说:“一旦有一天人们发现,逻各斯中心主义从来都是以不可告人的方式建立在阳具中心主义之上,从来都为维护男性秩序提供等同于历史本身的理由,一切又会如何?”由此,我甚至可以说,莉塞的疯狂是对于这一中心主义的反抗。
面孔作为莉塞疯狂的表征在小说的结尾处得到了疏解——当莉塞成功回到家中时,面孔以这样的方式回归到了秩序中,“孩子们的面孔挂回了原位,就像墙上的画一样。”至此,莉塞获得了病理学上康复的判定,重新回归到了日常秩序中。
疯狂与幻觉:被压抑的女性
小说虽然集中在莉塞变成疯人整个过程的塑造,可是其背后的零星渗透却暗含着莉塞变疯狂的蛛丝马迹。其中横亘着一个痛苦的词汇:压抑。莉塞的丈夫格特是一个大男子主义的典型,他认为莉塞作为作家的名声对于他个人是一种侮辱,而他十分热衷于让莉塞了解自己浪漫的征服史。而他的情人格蕾特自杀也不能让他感觉到惭愧。处于这种婚姻中的莉塞却被医生告知格特那些在婚姻中的越轨行为是替她做出的。“那是一种泄愤行为,就像两岁孩子把麦片粥弄洒一样。”……格特和莉塞都有复杂的神经症问题,这是医生给莉塞的诊断。莉塞对医生的看法不置可否,一方面表现出她对于医生看法的权威性依赖,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她似乎对此并没有波涛汹涌的反抗,而这些似乎都让一股邪恶的泉水渗透进她的内部——那就是压抑。压抑成为了莉塞病症的源头。“她总是重复格特或阿斯格的看法,仿佛她从未拥有过独立的思想。……只有在写作时,她才能表达自我,而她没有其他天赋。”格特是莉塞的现任丈夫,而阿斯格是她的前任,很显然,莉塞在一种被压抑的状态当中无法真正表达自己。这种被压抑正是女性歇斯底里症的成因。在此我们说莉塞的疯狂的主要成因来自于丈夫所代表的男性权利社会对于女性价值的压榨。虽然,莉塞已经是知名的儿童文学作家,但是她的丈夫依然认为这件事无足轻重,而莉塞因为医生的诊断也陷入到对于丈夫偷情行为的合理化解释当中,无意中将自我当成了丈夫偷情的原因。是因为“我”的神经症问题才会导致丈夫偷情的。这似乎是莉塞给丈夫偷情寻找的合理化借口。接下来是莉塞听到格特和吉特在厨房公开密谋如何除掉她……但是这些情节因为后来莉塞幻化自己世界的情形变得越来越难以确认究竟哪些是她的幻觉,哪些是真实。在此,小说家的笔触刻意将读者引入到莉塞一样的境地,即无法分辨真实与虚幻,这是这本小说的玄妙之处。即作者不知不觉间已经将读者裹挟进自己的病态时空,一时之间真实和虚幻的边界越来越模糊。这样,我们感觉到,从小说的一开始,所有的情节都可能是幻觉,我们不禁要问的是,什么才是真实?
我们陷入了一种泥塘,我们和莉塞一样想要像剃掉牛骨上的牛肉和筋膜一样分清眼前的这一切。但是我们随即会陷入到和主人公同样的无力感当中,因为我们早已经在还没有准备好,或者认为自己尚能把握一切的时候悄然滑入幻觉的深渊。正如莉塞的发问:“面孔究竟是在什么时刻分崩离析的呢?”
有关于他人的痛苦
迪特莱弗森这样的作家能够有能力绝不仅仅是让我们窥见一个曾经在精神分裂漩涡里挣扎的人的全部生存状态。不同于完全的虚构情节,迪特莱弗森因为自身所受到的病痛折磨因此可以勇毅地表现其经验世界。她的小说的深刻之处在于,她小说中的女性不但处于一个在家庭和婚姻当中身份撕裂的地位,同时也处于一个在广泛的社会当中撕裂的地位。暂且不说遍布于小说前后的对于社会政治议题的关注与讨论,单从小说最后一章中的一段对话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一更加宽广的视角(而这一视角绝不是点缀):最后一章中,因为被宣判为康复而返回到家庭秩序中的莉塞终于可以“开始写作,开始照顾孩子们”了,她说:“我经历了一场危机,我意识到一个人不能无视那些在世上受苦的人。”这让我想起瑞典电影导演英格玛·伯格曼的一部电影《假面》。《假面》中以女演员伊丽莎白拒绝说话这一反常行为为起点,而伊丽莎白拒绝说话是因为在电视上看到一个发生在遥远国度的残忍的自杀场面而出现的,《面孔》中莉塞的疯癫也有在“这一对人类普遍遭受的痛苦”的意义上发生的情节。这体现在小说中,莉塞对于他人的痛苦甚至越南战争的讨论当中。在此,“疯狂”不应当被单纯看作女性被压抑的结果,而应当在一个更加广泛的视角上去考察疯狂这一人类的异化形式。疯狂是对日常秩序的瓦解和消除,即用一种失序和脱序的状态去反抗日常当中的不合理秩序。“我经历了一场危机,我意识到一个人不能无视那些在世上受苦的人。”小说中作家借主人公莉塞之口反复说出此种议题。而有关于这个维度的观察和发现有助于我们避免将莉塞的疯癫变为一种私人性质的问题或者单纯女性主义的问题,找到那根更加隐形的线索……
而占据全书的另外一个令人印象深刻且发人深省之处是作者对于“写作”的强调,即当写作运动展开,莉塞的生活就处于一种可控制的理性范畴,而当写作这一运动受到阻滞,理性就无法建立它自己的秩序了。这里,迪特莱弗森借助莉塞之口,几乎将写作作为一种超越性手段(已经不仅仅是治愈这个被用为滥俗的意义上)成为女性获得自由的一道暗渠。这一点,正好暗合了,埃莲娜·西苏对于女性写作的定义。在《美杜莎的微笑》中,西苏强调了女性写作的重要性和作用,她说:“她必须写她自己,因为这是开创一种新的反叛的写作,当她的解放之时到来,这写作将使她实现她历史上必不可少的决裂和变革。”
(作者系诗人、翻译家)
 更多
更多

肖复兴:读书,是一辈子的事情
“第一本书的作用竟然这样大,像是一艘船,载我不知不觉并且无可抗拒地驶向自己意想不到的地方。”
 更多
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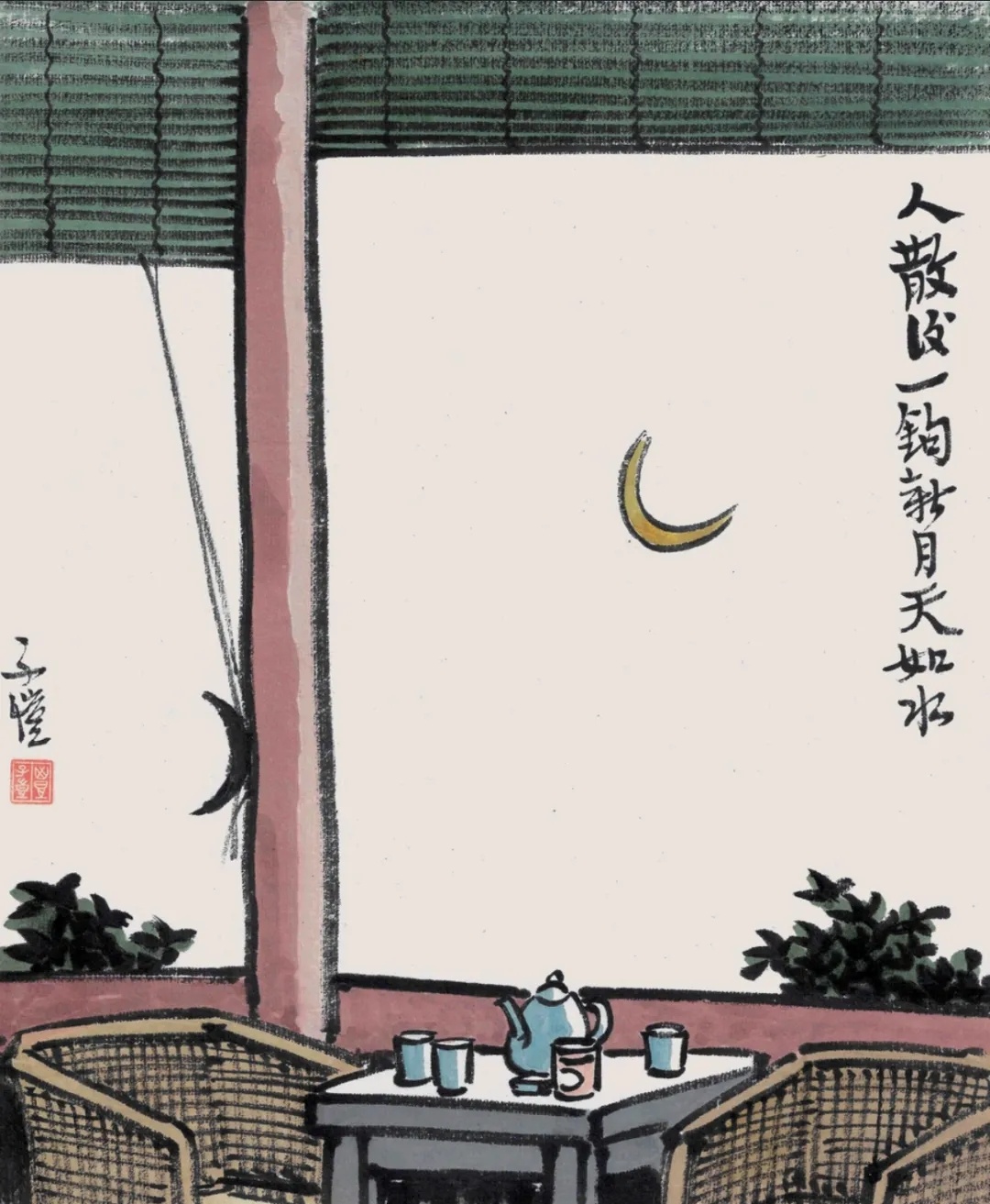
王军: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
“人的一生,遇上过多少个一钩新月天如水的夜?”
 更多
更多

散文 | 母亲的老布鞋
以“母亲的老布鞋”为线索,串联起母亲大半生的辛劳与温情,制作老布鞋的细节与爱意,以及象征意义。

散文 | 松魄千霜
本文以青衫客从初见的惊叹,到触摸时的感佩,到听涛时的共鸣与自省,再到对画松、听心、持守等问题的思考与回答,最后以充满敬意的告别作结,形成一个完整的欣赏与感悟历程。赋予松树

散文 | 爷爷
对爷爷的怀念

散文 | 公竟渡河
大禹劈山,北魏凿石,登天梯跃龙门,不是同一批人,却是同样的人。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倔强,那种九死无悔绝不丢盔弃甲的刚韧,那种不计成败敢在绝路中走出生路的孤勇,用河津话

诗歌 | 年轮之上(组诗)
中年之后,终于慢下来了 管理的园囿,越来越少 时间的绳索,一点点勒进躯体 生活的卷帙,著述颇丰 他们喟叹一声,年轮的指针 晃了晃,像不息的小小寰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