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非洲英语文学:身份、性别与历史的叙事变革
2024年的非洲英语文学展现了蓬勃的创作活力,新兴作家与成熟作家共同编织了一幅多元而深刻的文学图景。在这一年中,身份认同与文化传承、女性抗争与自由以及历史创伤与赎罪等主题成为作家们探索的核心议题。年轻作家们以敏锐的洞察力和独特的叙事视角崭露头角,他们通过创新的文学形式与语言,重新诠释了非洲的文化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张力;成名作家们则继续深入挖掘殖民遗产的深远影响以及后殖民时代的复杂挑战。通过文学的力量,非洲英语作家们正在重新定义自我、重塑身份,并在历史的回响与未来的憧憬之间,寻找属于非洲的声音与叙事。
身份的枷锁:文化传承与自我追寻
在后殖民时代,特别是在政治和社会动荡的背景下,非洲个人如何在现代现实中调和其文化根源与身份认同,成为了许多非洲英语作家的重要议题。尼日利亚作家佩米·阿古达(Pemi Aguda)的处女作短篇小说集《幽灵之根》(Ghostroots)、尼日利亚作家楚克乌布达·伊贝(Chukwuebuka Ibeh)的处女作长篇小说《祝福》(Blessings),以及加纳裔英国作家卡莱布·阿祖玛·尼尔森(Caleb Azumah Nelson)的第二部小说《小世界》(Small Worlds)(其处女作为出版于2021年的《开放水域》),都以各自独特的叙事视角探讨了这一主题。
《幽灵之根》入围了2024年美国国家图书奖小说奖决赛,小说集中的多个故事体现了个人身份与文化传承的主题,作品中的许多幽灵通过母系血脉传承:开篇的故事《显现》讲述了一段因一位女性在女儿脸上认出自己母亲的面容而变得紧张的关系;《母乳》的主人公轻易原谅丈夫的不忠,却背叛了自己母亲的遗产;《想象我背着你》中的母亲因一场悲惨的车祸而心神不宁,变得无精打采且充满攻击性,女儿不得不暂停自己的生活来照顾她;《女孩》中,一个被母亲送去工作的女儿在被绑架后,必须面对母亲的幽灵……故事中的人物在追求独立与自我实现的过程中,既渴望突破家庭和社会的束缚,又无法摆脱深深植根于文化和超自然领域的影响,她们常常发现自己被家庭的责任、社会的压迫,甚至是来自已故亲人的超自然力量所左右,小说特别突出了超自然力量与母爱的传统意义相结合的独特手法,呈现了文化身份如何在代际之间传递,以及这一过程中的情感纽带如何变得错综复杂。
《祝福》的聚焦点在于个体如何在复杂的社会冲突和家庭纷争的夹缝中寻求家庭、社会和国家层面的认同与归属感。小说入围了2024年威尔伯·史密斯探险写作奖候选名单。小说主人公奥比弗纳与家人生活在尼日利亚的哈科特港市,他15岁时,父亲带回家一个年轻的男性学徒阿博伊,奥比弗纳和这位学徒产生了暧昧的情愫,父亲将阿博伊赶出家门,并将儿子送到一所宗教男校。在这所学校里,奥比弗纳遭受着种种考验,“在那广阔的神学院里,他感到与世隔绝,被一种纯粹而亲密的平凡感所淹没。即使他竭尽全力尖叫,也没有人会听到他”。在故事的前半段,奥比弗纳时刻面临“你是谁”的内心拷问,而在故事的后半段,奥比弗纳则纠结于“如何在世界中确定你的道路”这一难题。
《小世界》同样涉及自我身份的主题。该作荣获2024年迪伦·托马斯奖。这部成长小说跨越三年,分为三个部分,就像爵士三重奏中的钢琴、贝斯和鼓手。第一部分中,斯蒂芬和他的朋友们刚刚结束学业,正在决定下一步该做什么。斯蒂芬的人生道路发生变化,他面临着分离,甚至无法从他的乐器中找到慰藉。第二部分中,斯蒂芬与他的朋友一起接受厨师培训,生活的节奏重新回归。第三部分中,斯蒂芬休假前往加纳:“最近,我感到一种渴望更多的冲动。我一直对自己是谁或我可能在哪里找到自己有一个不错的把握,但我从未真正知道自己来自哪里。这次旅行开始了一个转变。我的父亲可能会用他自己的故事填补这些空白。我想让他告诉我他是谁,或者他曾经是谁。我想知道他在二十岁时是谁。我想知道他的梦想是什么,他在哪里找到自由。”故事最终圆满结束。
上述三部作品虽然叙事风格和背景各异,但都围绕着身份认同与文化传承这一核心主题:阿古达通过超自然元素与母系传承的交织,揭示了代际之间的情感纽带与文化传递的复杂性;伊贝通过主人公在家庭、宗教和社会压迫中的挣扎,探讨了个体如何在多重冲突中寻找自我;尼尔森通过主人公的成长与寻根之旅,展现了音乐、家庭和历史如何共同塑造个体身份。
抗争与重生:女性文学中的身份、权力与自由
在当代非洲英语文学中,女性作家正以独特的叙事视角和深刻的社会洞察力,重新定义非洲文学的声音与边界。获得2024年凯恩非洲写作奖的作家为来自南非的纳迪娅·戴维德(Nadia Davids),获奖作品为短篇小说《驯服》(Bridling);获得2023年非洲文学岛屿奖的为苏丹作家蕾姆·贾珐(Reem Gaafar),其获奖作品为处女作小说《满嘴都是盐》(A Mouthful of Salt);另外还有博茨瓦纳女作家特洛托·查马赛(Tlotlo Tsamaase),她的处女作小说《子宫之城》(Womb City)将科幻与恐怖元素相融合,呈现了一部扣人心弦的非洲未来主义叙事作品。
《驯服》刻画了女性在面对历史遗留的种族创伤、根深蒂固的性别不平等以及隐形的权力结构时所展现的坚韧与抗争。作品中的女性角色不仅在个人生活中努力寻找自我认同,还在社会层面挑战既有的压迫性秩序,试图在破碎的历史与现实之间开辟属于自己的空间。故事的叙述者是一位年轻但已颇具经验的女演员,她与一群来自不同背景的女演员共同生活与工作,其中既有年轻的理想主义者,也有历经沧桑的年长者。一位年长的女演员以充满智慧的口吻告诫叙述者:“仅仅因为他们要求流血,并不意味着你必须给。”这句话不仅成为故事的核心隐喻,也揭示了女性在面对压迫时的自主选择与反抗精神。凯恩非洲写作奖评委会主席奇卡·乌尼格韦(Chika Unigwe)高度评价《驯服》,称其为“一项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是语言、叙事和冒险精神的胜利。它体现了凯恩奖的精神,即庆祝非洲作家短篇小说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并挑战非洲文学的单一叙事”。
《满嘴都是盐》是一部深情讴歌非洲-阿拉伯女性身份与命运交织的史诗之作。小说以细腻而富有张力的笔触,勾勒出三位苏丹女性在四十年间命运的交织与碰撞。故事始于1980年代的北苏丹,一个表面宁静如田园诗般的偏远村庄,却在命运的捉弄下接连遭遇一系列令人窒息的悲剧。首先,村庄的平静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溺水事件打破——苏拉发唯一的孩子被认为是溺水死亡。苏拉发是一夫多妻制中的第一任妻子,长期忍受着丈夫的冷漠与暴力,以及婆家的无情欺凌。紧接着,村庄的牲畜被一种神秘而致命的病毒席卷,成群的牛羊在痛苦中倒下。当村民们试图焚烧这些牲畜的尸体时,一场失控的大火吞噬了村庄赖以生存的椰枣园。更离奇的是,一名年轻女孩在婚礼前几天死于一场离奇的事故。在这片被悲剧笼罩的土地上,14岁的法提玛正等待着即将公布的考试成绩。她是一个叛逆的少女,对家人为她安排的近亲婚姻毫无兴趣。她深知,教育是她逃离村庄、摆脱命运枷锁的唯一途径。然而,接踵而至的灾难威胁着她的计划。法提玛的命运与娜玛琴紧密交织。娜玛琴是一位几十年前从南苏丹嫁到法提玛村庄的女性,她的一生被殖民政策、南北苏丹的矛盾以及奴隶制废除后依然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所裹挟。在这片多变的土地上,三位女性以不同的方式寻求着个人的自由与尊严。她们勇敢地质疑那些束缚她们的历史与社会预设,试图在现代化的浪潮中为自己重新定义空间与身份。
《子宫之城》是一部深刻探讨人工智能、监控、女性身体权与社会阶级之间复杂关系的非洲未来主义小说。故事设定在多年后的博茨瓦纳,一个高度控制且资源分配极度不平等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个人的身体被政府视为一种可操控的资源,而掌控女性身体的权力则成为巩固父权结构和社会等级制度的重要工具。科技的进步使得政府能够重新利用各种人体,这些“躯壳”被用来容纳其他等待名单上的灵魂的意识。罪犯的身体则通过微型芯片进行严密监控,以确保他们的错误行为不会重演。28岁的奈拉是一名成功的建筑师,与她的警官丈夫埃利法西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然而,奈拉的身体曾属于一名罪犯,这使得她的存在始终处于监控之下。由于奈拉可能出现的“偏差行为”,她的丈夫埃利法西被赋予了控制她精神和身体能力的权力。此外,埃利法西还掌握着一项秘密能力——通过遥控装置激活奈拉的欲望。尽管奈拉的存在被微型芯片所控制,她仍然能够体验到强烈的情感,尤其是对拥有一个孩子的渴望。在经历了一系列流产后,奈拉和埃利法西向一家生育诊所寻求帮助。他们的女儿通过“精心设计”的胚胎在诊所的“子宫培养箱”中成长,奈拉则通过智能手机充满爱意地注视着婴儿的发育过程。然而,这一看似美好的过程隐藏着一个残酷的陷阱:如果未能按时付款,子宫孵化器会被迅速而无情地关闭。这种经济压力加剧了奈拉和埃利法西之间日渐衰弱的婚姻关系,而奈拉与一位富商贾尼斯的婚外情更是让这段关系雪上加霜。一次意外事件彻底改变了奈拉的命运。在一次疯狂飙车中,奈拉和贾尼斯撞死了一名女子。出于恐惧,他们选择埋尸灭迹,试图掩盖罪行。然而,这一行为引发了一系列不可控的后果:受害者的复仇之魂从坟墓中归来,开始追杀奈拉所珍视的每一个人。为了逃脱诅咒并确保她的孩子存活,奈拉必须在幽灵和政府的双重追捕下,揭开受害者死亡时正在调查的黑暗政治阴谋的谜团。小说将《女仆的故事》中的政治压迫与《逍遥法外》中的社会控制主题巧妙融合,通过奈拉的命运展现了女性在科技与父权双重压迫下的挣扎与反抗。
戴维德通过戏剧化的叙事揭示了南非后种族隔离时代的隐形压迫;贾珐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苏丹女性在历史与社会约束中的挣扎与抗争;查马赛则以科幻与恐怖元素为框架,反思了女性身体自主权与科技控制的未来困境。这些小说通过不同的叙事风格——从现实主义到科幻题材——不仅揭示了非洲社会中的历史遗留问题,还展现了女性在压迫与抗争中寻找自我、重塑身份的力量。
历史的重量:战争与隔离中的赎罪与真相
历史与记忆是塑造个体与集体身份的重要力量,尤其是在经历过战争、殖民与种族隔离等深刻创伤的社会中,这种力量显得尤为沉重。尼日利亚作家奇戈齐·奥比奥马(Chigozie Obioma)的小说《乡村之路》(The Road to the Country)与南非作家凯伦·詹宁斯(Karen Jennings)的作品《扭曲的种子》(Crooked Seeds)都以历史为背景,探讨了个体如何在国家与家庭的创伤中寻找自我、承担责任并寻求救赎。
《乡村之路》以20世纪60年代末的尼日利亚为背景,此时的尼日利亚是一个饱受历史创伤的国家。故事的主人公昆勒无意中听到母亲说他被诅咒了。在她看来,他的疏忽导致了一场车祸,差点害死了他年幼的弟弟通德。多年后的1967年,昆勒刚刚大学毕业,得知弟弟和一个女人搬到了比夫拉。出于内疚和对弟弟安全的担忧,昆勒自愿加入了一个红十字会组织,这是尼日利亚人安全进入该地区的少数途径之一。不幸的是,昆勒与团队失散,被比夫拉士兵发现,并被迫加入其军队。随着内战的爆发,昆勒的弟弟在混乱中失踪,昆勒被迫接受了一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救回失踪的弟弟。他的寻找之旅不仅是一个生死未卜的营救行动,更逐渐演变成一段深刻的赎罪之旅,昆勒“饮尽了战争的苦水”,他的每一步都与他对战争的认知、对兄弟情谊的承诺以及对自身历史的反思紧密相连。同时,故事也通过当地一位神秘的预言家对昆勒的预言——“死而复生”的命运,增添了神话般的色彩和哲学层面的深意。
《扭曲的种子》试图解答在暴力与不公正中生活的后代,如何面对被遗留的集体记忆与负担,让读者思考历史的影响、民族的责任以及个体如何在负担重重的过去中寻找出路。小说的主人公,53岁的迪尔德丽·范德文特生活在一个近未来世界,这个世界面临严重的水资源短缺,且充斥着火灾和飘落的灰烬。作为一位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妇女,她的家庭和个人生活无法逃脱过去的阴影,那些早已被遗忘的记忆逐渐浮出水面,主人公必须面对她家族的过去,他们可能对种族隔离政权下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没有直接责任,但他们需要面对发生在他们眼皮底下的真相。小说结尾处,迪尔德丽问警官马邦博,几十年后的现在,追究这一切有什么意义。他回答说:“范德文特小姐,这对你来说当然很难,但你必须同意,真相必须大白于天下。置之不理就是否认和掩盖。我们还必须考虑其他相关的人。许多家庭失去了他们的孩子,多年来一直生活在疑问和痛苦中。”
奥比奥马通过昆勒的内战经历,展现了战争对个人与家庭的深远影响,以及赎罪与救赎的可能性;詹宁斯则通过迪尔德丽对家族历史的追问,揭示了后种族隔离时代南非社会的集体记忆与个体责任。两部作品都强调了直面历史真相的重要性,无论是为了个人的救赎,还是为了社会的和解。
从身份认同与文化传承的探索,到女性抗争与自由的呐喊,再到历史创伤与赎罪的反思,这一年的非洲英语文学一方面揭示了非洲社会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另一方面也回应了全球范围内普遍关注的人类议题。新兴作家以大胆的实验精神和敏锐的时代触觉,为非洲英语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而成熟作家则通过深刻的历史视角和细腻的社会观察,进一步深化了其厚度与广度。随着非洲英语文学作品在国际奖项中屡获殊荣,非洲英语文学的影响力正日益扩大,不仅为非洲本土的文化表达提供了丰富的载体,也为世界理解非洲的历史、现实与未来打开了新的窗口。
(作者系北京大学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世界文学》编辑)
 更多
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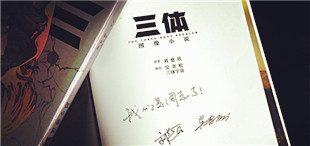
吴青松:我把画《三体》当成是一场修炼
“我把画《三体》当成是一场修炼,修炼可以为之后的创作提升能力,同时在其间隙,也能为之后的创作做好更充分的准备。”
 更多
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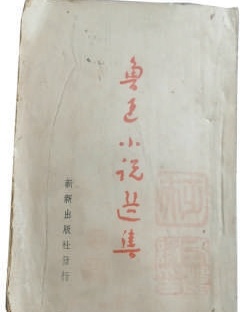
石舒清:三本书的收藏记忆
记得大概十年前,我买到一本版本很是特别的《忠王李秀成自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