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学敏:在时代“飞行”中重塑诗意航道
原标题:最新诗集《经济舱》出版 龚学敏:在时代“飞行”中重塑诗意航道
“这是抵达心灵的诗歌飞行。”翻开诗人龚学敏的最新诗集《经济舱》,封面上的这句话,仿佛是一把钥匙,开启了一个充满隐喻与哲思的诗意世界。
2025年初,这本由重庆出版社出版的诗集一经问世,便在文学界激起层层涟漪。它精选了龚学敏近年来创作的167首诗作,其中大量作品从未公开发表。这些诗作以独特的视角、灵动的意象和细腻的笔触,构建起一个工业文明与存在主义交错的诗意宇宙。
“经济舱”里的时代隐喻
谈及为何以“经济舱”命名这本诗集,龚学敏表示:“‘经济舱’的意义早已超越了出行的界限,它象征着我们共同乘坐在人生旅途中的时代飞船。”在他看来,如今的地球就像一个经济舱,人类在其中高速前行,探索着未知的未来。这个独特的隐喻,既是对农耕文明诗意的突破,也是对现代人悬浮生存状态的深刻凝视。
翻开诗集,读者会发现其中并无一首名为《经济舱》的诗,可“经济舱”却无处不在。诗集中,航站楼中的吸烟室、冬天的高铁、邮筒、药铺、皮卡车等细节、场景频繁出现,这些现实化细节、场景成为了诗人构建诗意的桥梁。
如在《乌云》中,龚学敏写道:“机舱里常温的脸谱,对着散装的光芒/有时,光芒们只是一个个形容词而已/如同,感冒药中被捣碎的/两粒VC”,以反讽的语调揭开生活的面纱,展现出生活的荒诞与真实。
对现实的“锐利切入”
2025年3月,两场研讨会在重庆、成都相继举行,学者、作家、评论家齐聚一堂,探讨《经济舱》的艺术特色、思想内涵及其在场意义,龚学敏笔下介入现实、落于烟火的文字,发人深省。
在不少评论家看来,龚学敏在诗集中展现出对现实的“锐利切入”,绝非处理小情绪,而是深入挖掘时代的核心问题,如社会矛盾、人性困境等。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胡弦直言,优秀诗歌应兼具技术性、思想性与社会性,成为建设性力量,龚学敏肩负着这样的诗歌使命,不断拓展着诗歌表达的边界。
在《经济舱》里,读者能看到真实的生活景象,嗅到浓浓的“烟火气”。青年批评家李壮对诗中描写飞机场、吸烟室、空姐、高铁车厢、加油站等细节、场景印象深刻,他从中感受到生活最本真的样子。巴金文学院负责人干海兵同样认为,《经济舱》立足时代现实,在烟火中彰显人性经验及道德操守,龚学敏能从相对芜杂宽泛的世象题材中开辟出明晰的审美路径,尽显中年况味,见情见真。
重构当代诗歌价值
《当代文坛》杂志社负责人赵雷指出,《经济舱》以双重维度重构了当代诗歌的价值。在文本层面,它将高铁、加油站等“时代零件”与古典意象交融,开辟出独特的“新鲜审美经验”;在创作史层面,龚学敏始终在现代性中践行“永远在路上”的探索,拥抱飞行、AI等新事物的冲击。
在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时代,诗歌的创作与价值也面临新的审视。西华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王学东从“经济舱”联想到李贺的驴背、谢灵运的山水、波德莱尔的拱廊街,认为它们都烙印着行走的诗学基因,而龚学敏重构了“行走”的当代定义:飞行即新的步行,诗歌是隐形的翅膀。
从《九寨蓝》《长征》中“狂飙突进”的语言爆发,到《经济舱》中“大道至简”的沉淀,龚学敏的诗歌创作不断蜕变。正如干海兵形容的那样,这种变化如同激流归于深海,看似平静,实则蕴含着更为深沉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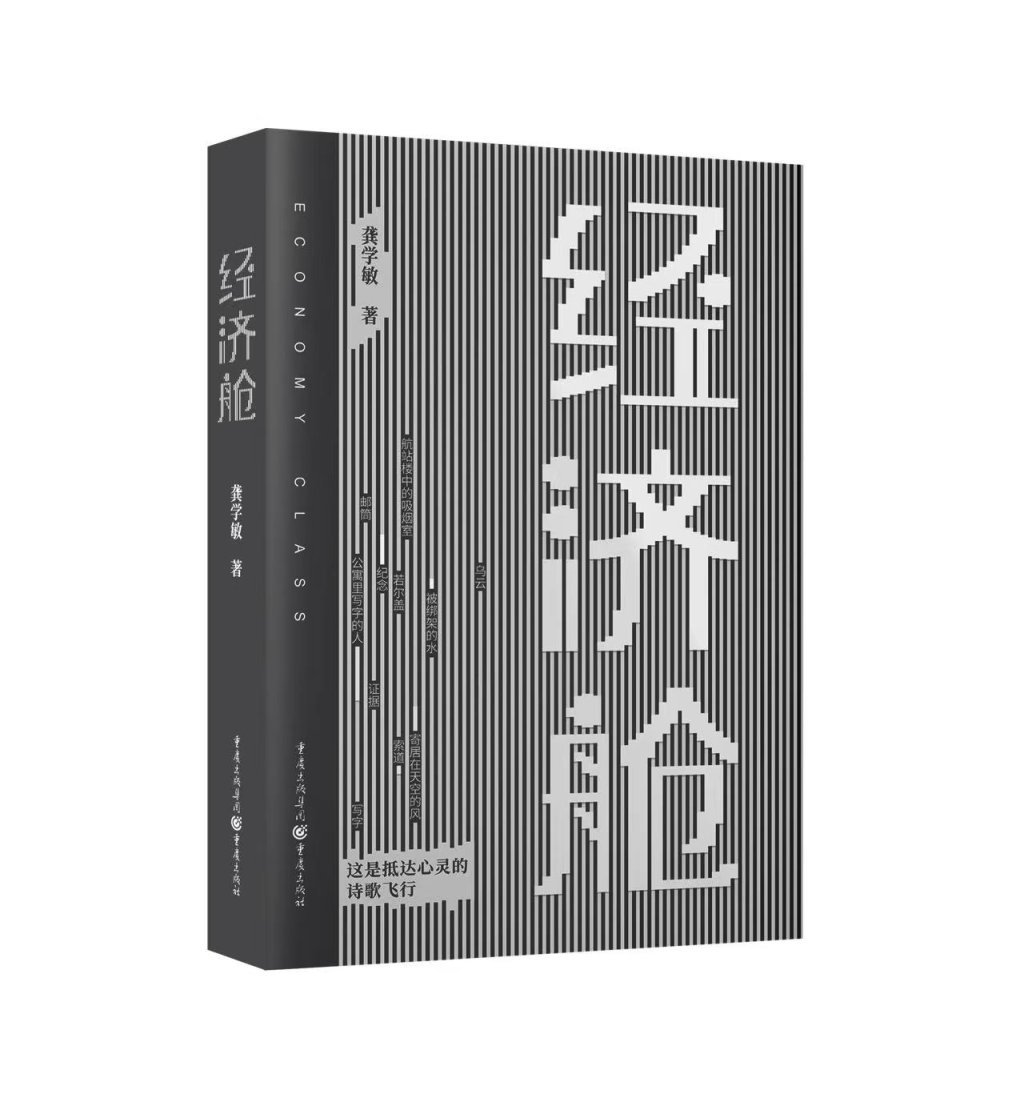
【访谈】
3月14日,“龚学敏诗集《经济舱》研讨会”之后,带着对其创作历程、诗歌理念以及未来展望的诸多好奇,记者与龚学敏面对面,开启了一场深度专访,一同探寻他在诗歌创作之路上的独特风景与深刻思考。
聚变,从“地球村”到“经济舱”
记者:新诗集《经济舱》的命名极具现代感,为何选择“经济舱”这一意象作为核心隐喻?里面并没有一首诗叫《经济舱》。
龚学敏:《经济舱》选择“经济舱”作为核心隐喻,源于当下时代的深刻印记。如今,快节奏生活成为常态,飞机、高铁成为人们出行的常见选择。在经济舱、候机厅或高铁上,人们在奔波途中开启阅读、思考,不少诗歌便在此诞生,这是时代在文学创作领域的生动注脚。很多人在飞机上阅读,沉浸在文字的世界里,这种生活场景成为诗歌创作的独特土壤。
从宏观角度看,约60年前,“地球村”概念因经济发展、交通电讯便利而诞生,那时人们觉得世界紧密相连如同村落。但如今,互联网与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地球村”已无法精准描绘当下社会形态。当下的地球更似一个巨大的“经济舱”,人与人虽共处其中,却各自朝着未知探索。在经济舱中,人们相互独立又彼此关联,这种状态恰如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生存模样。“经济舱”这一意象,反映了现代社会人们的生存状态,所以被选定为诗集的核心隐喻。
记者:167首诗被收录其中,在创作它们的时候,灵感来源是什么?
龚学敏:这些诗是我近几年创作的成果,以《经济舱》命名,旨在反映生活状态、聚焦现实。创作灵感并非仅源于经济舱,尽管它是现代生活的一个特殊场景,但只是众多灵感来源的一部分。生活是一座丰富的宝藏,日常的各种场景与现象,从街头巷尾的琐事到社会发展的重大变革,都是灵感的源泉。诗集着眼于当下,是对现实生活细致观察与深入思考的结晶,经济舱之外,生活的广阔天地为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
记者:诗集里有很多内容,比如空姐、高铁、加油站等,但您也同时写到了桂花、水杉、古镇、群山……就有一种现代与古典并存的奇妙观感。您是作何思考的?
龚学敏:随着时代的发展,农耕文明发生了巨大变化。以油菜花为例,过去人们看重其榨油的实用价值,将其作为农作物满足生活需求。如今,春天里油菜花田成为人们休闲观赏的景观,带来的愉悦和审美体验远超其作为农作物的价值。这表明传统农耕文明的诗意在当下已发生深刻转变。
我们正处于农耕文明、工业化、信息时代、人工智能相互叠加的大变局时期,诗歌创作应紧跟时代步伐,关注新事物、新现象,用新视角和语言展现生活。我在诗集中将现代元素与古典意象交织,就是为了反映当下现实生活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呈现时代的独特风貌。
调整,让诗歌更契合时代精神
记者:诗集中很多诗都在直面现实,总体色调比较冷峻,对比您之前的浪漫主义风格,这是否意味着您的诗学观念在发生转变?在审美取向上的突破?
龚学敏:写作观念和风格的演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当今世界瞬息万变,作家和诗人若不与时俱进,必然被时代淘汰。无论过去成就多高,若仍遵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前的写作模式和思维方式,就难以在当下立足。
当下社会充满不确定性,大数据等新兴事物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诗歌不仅要发展更需改革。在形式上,不能再墨守成规;在写法上,要对当下出现的词汇、社会现象做出新颖且具前瞻性的判断。这种变化是我为适应时代发展,在诗学观念和审美取向上做出的调整与突破,让诗歌更契合时代精神。
记者:从语言上来看,《经济舱》里的每个句子,都有着您一贯的风格,比如闪烁跳跃、想象无限,充满烟火气,但这次似乎多了很多怪诞和机智,就像有老师评价您是个内心狡黠的人,这次是一次更深度的释放和发力吗?
龚学敏:现实世界充满荒诞离奇的元素,这些元素激发了我的创作灵感。如今,社会上出现了许多难以想象的现象,像《哪吒2》票房的惊人成绩、Deepseek的突然诞生,以及春节期间人们关注点的骤然变化,都颠覆了传统认知和生活模式。如果作品不能反映这种现实的荒诞,就说明没有真正触及生活的本质。我深知作为写作者,必须敏锐感知周围世界的变化,将荒诞现实融入作品。所以在《经济舱》中,我更充分地展现了怪诞和机智的风格,这是对现实的真实映照,也是创作上的一次探索与发力。
诗歌,写当下更具难度
记者:在研讨会上,多位评论家都提到了您对现实的“锐利切入”。您怎么看?
龚学敏:在我看来,诗歌与现实紧密相连,不介入现实的诗歌缺乏生命力。诗歌的本质在于反映生活,关注社会现象,抒发人们的情感和思考。当今时代变化迅速,诗歌若与现实脱节,就会变得空洞无物。我们应用诗歌记录时代,思考现实问题,这样诗歌才能充满活力,成为时代的见证者和思考者。
记者:诗集中多次出现行李箱、安检通道、航班延误等细节、场景,它们既具体又充满象征。您如何把握日常细节与宏大隐喻之间的分寸?是否担心过于具象会限制读者的想象?
龚学敏:行李箱、安检通道、航班延误这些细节、场景是生活中常见的画面,我将它们写进诗里,旨在通过这些具体事物传达更宏大的主题,如人们的生活状态、社会的发展变化等。把握日常细节与宏大隐喻之间的分寸并不容易,我会努力将自己对这些细节的感受和思考融入其中,使它们自然地与宏大隐喻相融合,让读者能从细节中体会到深层含义。
我并不担心过于具象会限制读者的想象。因为每个人的生活经历不同,对这些细节的感受也会不同。读者在阅读时会结合自身经验进行理解和想象,可能会从具体描写中挖掘出更多独特的内涵,丰富阅读体验,拓展诗歌的意义空间。
记者:之前您写《紫禁城》《纸葵》《钢的城》都充满历史厚重感。这次却与当下无限接近,对一个诗人而言,回望与直视,哪一个更难?
龚学敏:相对而言,写历史题材会轻松一些。历史有固定的框架和大众普遍的认知度,创作者形成自己的历史观后,可依据框架抒发对历史的感悟,更多地是表达主观感受。当然,历史也可以解构。
而写当下则面临更多挑战。写当下需要先对复杂的现实现象做出判断,挖掘其中的价值和意义,并融入作品。当下社会发展迅速,同一件事不同人看法各异,创作者还需有预见能力,否则作品可能很快失去时效性。所以,在我看来,写当下更具难度。
记者:《纸葵》出版的时候,很多读者说看不懂。您回应说在创作时也挺烧脑。您觉得《经济舱》好读吗?它是否能替代《纸葵》,成为您最满意的作品?
龚学敏:我认为《经济舱》相对好读一些。《纸葵》基于三星堆出土问题,对一种文明状态进行想象和表达,充满了想象空间,理解起来有一定难度。而《经济舱》描绘的多是现实生活场景,大家更为熟悉,理解起来相对容易。
至于《经济舱》能否替代《纸葵》成为我最满意的作品,很难简单评判。《纸葵》在想象构建上让我十分满意,为我打开了新的创作视野。《经济舱》则在对现实的洞察和思考方面给了我新的收获。目前来看,它们在不同方面都让我满意。
诗刊,找到平衡成为微光
记者:您担任《星星》诗刊主编多年,见证诗歌生态变化。如今短视频时代,诗歌常被简化成“金句”传播。您如何看待这种快餐化现象?
龚学敏:在短视频时代,诗歌被简化成“金句”传播,这与过去诗歌产生成语有相似之处,但本质不同。过去诗歌产生成语,是对诗歌内涵的高度凝练和传承。如今大家传播和接受得更多的是诗歌的副产品——诗意,而非诗歌本身。一首优秀的诗歌具有完整的结构和丰富的内涵,绝非简单两句金句就能代表。现在很多人只传播诗歌中最具诗意的两句,无法展现整首诗的价值。但这是时代发展的结果,我们虽无法改变,却可努力保持诗歌的完整性,引导大家深入了解诗歌。
记者:《星星》诗刊近年力推年轻诗人,但大众仍常抱怨“读不懂新诗”。作为主编,您认为诗歌刊物该如何在先锋性与可读性之间平衡?是否担心过分迎合读者会削弱诗歌的锐气?
龚学敏:诗歌刊物需要在先锋性与可读性之间找到平衡。保持先锋性很重要,它鼓励诗人探索新的表达形式和内容,推动诗歌发展。但同时也要考虑可读性,若诗歌过于晦涩难懂,便难以传播。在选稿时,可兼顾两者,既选取具有先锋性、勇于创新的作品,为诗歌发展注入活力;也挑选相对通俗易懂的作品,让更多读者走进诗歌世界。
过分迎合读者确实可能削弱诗歌的锐气,使诗歌失去独特的思想和艺术价值。所以在平衡先锋性与可读性时,要把握好度,在吸引读者的同时,坚守诗歌的本质和艺术追求。
记者:《星星》诗刊始终保持着对民间诗人的关注。在流量为王的时代,诗歌刊物如何真正成为公共精神生活的“灯塔”?
龚学敏:在流量至上的时代,这是一个极具挑战的问题。我们尽力拓宽诗歌刊物的视野,发表不同风格、不同背景诗人的作品,增强刊物的包容性,涵盖多元声音和观点。同时,更加关注社会现实,挑选能引起大众共鸣的作品发表,引导读者思考社会现象和人生价值。虽然难以再现过去诗歌全民热爱的辉煌,但我们希望诗歌刊物能在当下发挥作用,成为照亮大家精神生活的微光。
继续,关注现实期待新的突破
记者:近年来,您的创作历经多次转型,《经济舱》是否标志着新的阶段?未来可能走向何方?
龚学敏:从现实意义上讲,《经济舱》与我以往作品相比,确实呈现出新的变化。它更贴近生活,让我对现实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和判断,可以说标志着我创作的新阶段。
今年出版社还将出版我的新书《白雪与挽歌》。这本书聚焦东北抗联的历史。在我看来,写历史也是反映现实的一种方式,因为历史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下。
未来,我可能会延续《经济舱》关注现实的风格,继续深耕现实题材。但文学创作充满不确定性,生活中的灵感可能会促使我做出新的尝试和突破。我会保持对生活的敏锐感知,顺应灵感的指引,探索更多创作可能。
记者:近年来,您也在诗歌之外尝试着多种文体的创作,《吃出来的人生观》还将李商隐的诗翻译成一本白话文诗集。这种左手文右手诗的创作会一直持续吗?
龚学敏:随着年龄增长,我的创作节奏可能会放缓,因为想象力会有所减退。但我对社会和生活的思考会更深刻,当想象力不足以表达我的思考时,我可能会借助其他文体,比如小说来反映我的感受。所以这种左手文右手诗的创作可能会持续,但形式可能会变化,主要取决于我的表达需求。
记者:罗伟章《谁在敲门》改编的话剧正式上演了,在国内根据小说改编的文艺形式很多,这也让小说有了更多元的传播途径。您觉得诗歌可以有其他方式进行传播吗?未来诗歌发展趋势会怎样?
龚学敏:诗歌当然可以有其他传播方式。以前诗和歌不分家,现在流行音乐里也有很多有诗意的歌词。但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诗歌核心的表达或许还是要靠文字。和画家、音乐家跨界合作有一定可能性,不过诗歌有其独特的表达,其他艺术形式可能难以完全展现诗歌的内涵。但这种合作能吸引更多人关注诗歌,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
未来诗歌可能会更加多元化,与各种艺术形式的融合会增多,也会更关注现实和人类的内心世界。
记者:您曾说“AI已给诗歌创作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不知道现在的诗歌是不是进入了末路,但是,现阶段的AI已经强大到我们太多太多的写作已经毫无意义了。”为什么会这样认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写作?
龚学敏:如今,AI发展迅猛,很多人认为写作需要情感,可科学家都尚未完全明晰情感的本质。未来,人工智能或许比人类更了解自身,比如在照顾孩子方面可能比妈妈更精准。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与人之间关系冷漠,沉迷手机,交流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传统写作似乎失去了意义。
我们需要的写作,是充分发挥人类想象力、智慧和精神力量的写作。不应局限于单一方向,要敢于突破常规,探索各种创作可能。我们应尝试与人工智能共同构建新的文学生态圈的新可能,展现人类创作的独特价值。













